莫慧旋

2004年底—2005年初,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内出土了一百多枚南越国木简,填补了广东地区简牍发现的空白。考古发掘简报公布了有代表性的16枚木简,其中118号简的简文释读为:“适令穿哭颈皮,置卷鬬其皮,史福有可(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黄展岳研究员在《南越木简选释》中出提“哭”应为“兕”,“穿”引申为刺杀,“穿兕颈皮”意为剥杀兕的颈皮,“置卷鬬其皮”应是制作兕甲过程中的硝皮工艺,“史福”为人名。

兕的名实之辨
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名同而实异的例子比比皆是,如“甲”又名“铠甲”,是古代将士用于保护身体的防护装具。先秦时期,皮革制成者称为“甲”,铁制者称为“铠”,唐宋以后,不分材质,统称“铠”“甲”,或者连称“铠甲”。《周礼?夏官?司甲疏》:“古用皮,谓之甲。今用金,谓之铠。”可见“名”与“实”之间的相辨一直都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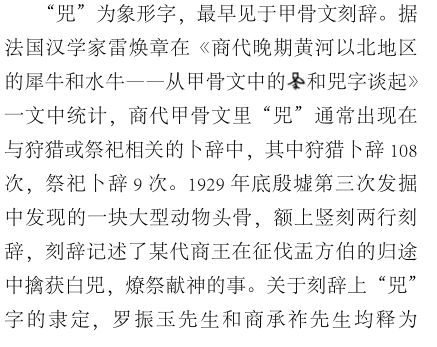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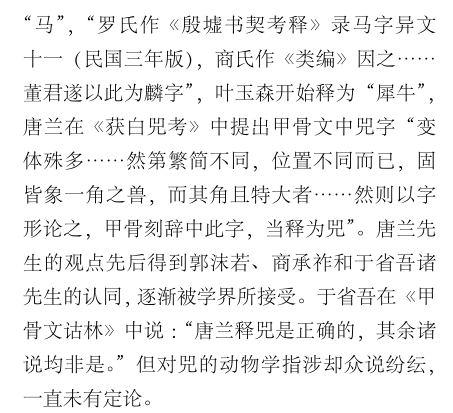
关于“兕”的名实之辨自古有之。先秦《尔雅》、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东汉郑玄《仪礼注》、东晋郭璞《山海经注》、唐刘恂《岭表录异》、南宋罗愿《尔雅翼》、明李时珍《本草纲目》等不同时代的文献都对这一命题有所涉及,见解各异,归纳起来,主要有牛属和犀属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先秦至汉代的文献中,兕多与牛类比,如《尔雅?释兽》:“兕似牛”,《说文解字》:“兕如野牛而青色”,《仪礼?乡射礼》注:“兕,兽名,似牛一角”,《山海经?南山经》注:“兕亦似水牛”等。而犀则多与豕类比,如《说文解字》和《尔雅?释兽》“犀似豕”。且兕常与犀相提并论,由此可知在当时人们的认知中兕非犀,而是一种外形与牛相似的猛兽。
晋代以后的文献中,兕、犀被逐渐混为一谈,兕即犀的观点被普遍接受,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分化出几种不同的说法。或认为兕为一角在额上的犀牛,唐刘恂《岭表录异》:“一在额上,为兕犀”;或认为犀之雌者为兕,南宋罗愿《尔雅翼》:“兕,似牛一角,青色,重千斤。或曰:即犀之?者”;或认为兕、犀为古今南北的不同称谓,《尔雅翼》:“古人多言兕,今人多言犀,北人多言兕,南人多言犀。”几种说法均难以自圆其说,众说纷纭,这似乎表明时人对兕为何种动物已不甚了了。
直至现代,关于兕为牛属还是犀属仍存在争议。持牛属说观点的学者有董作宾、陈梦家、张之杰和法国学者雷焕章等。董作宾在《“获白麟”解》中据德日进鉴定上述殷墟出土带刻辞的大型动物头骨上的牙齿为牛牙,并通过考证麟与牛的关系,提出兕即印度瘤牛;陈梦家在《殷墟卜辞综述》中提出:“卜辞的兕当是野牛”;雷焕章结合甲骨文的相关材料、古生物学家的鉴定意见以及先秦至两晋文献,得出兕为野水牛的结论;张之杰在《雷焕章兕试释补遗》中根据兕觚、岩画资料以及青铜狩猎纹、汉画和文献资料推断殷商至两汉,兕均可能是指野牛。
持犀属说观点的学者有丁山、姚孝遂、于省吾等。丁山在《商周史料考证》中认为:“犀兕一声之转,二兽一物,不过是方俗的殊名”;姚孝遂、肖丁在《小屯南地甲骨考释》中提出:“兕、犀乃古今字,今通称犀牛。……《尔雅?释兽》等即以‘犀’‘兕’相对为言,是误以兕、犀为二物,其由来已久。《尔雅》《说文》以似牛者为兕,似豕者为犀,强为区分,不可据”;于省吾在《甲骨文诂林》中提出:“《说文》以兕、犀分列,实本同字。兕为象形,犀则为形声。旧说以独角者为兕,二角或三角者为犀,《考工记?函人》:‘犀甲寿百年,兕甲寿二百年’,实则今通称之曰‘犀牛’而无别”;文焕然等在《中国野生犀牛的灭绝》中提出,小独角犀角较短,雌者多缺,体色为暗灰色,看上去很像青色或苍色。《尔稚?释兽》:“兕似牛”。晋郭璞注“一角,青色,重千斤”显系指此。近年亦有学者提出新的见解,黄家芳在《“兕”非犀考》中认为兕非犀,而是一种大独角、皮厚、外型似牛的群居动物。
探究兕的名实之辨出现的原因,大概是由于千年间气候变化、环境变迁以及人类过度捕猎致使兕在汉代前后灭绝,国内的野生犀牛分布范围也从秦岭淮河不断向南方缩小,以至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终灭绝。历代学者在看不到实物的情况下,根据前人笼统的记述寻找兕的对应物,或盲人摸象般根据前人“一角”的记述将其与名字发音相似的独角犀等同起来,或将其描绘成现实不存在的独角神兽。杨龢之在《中国人对“兕”观念的转变》中提出,春秋以前国人认知中的兕应为亚洲水牛属动物,战国始出现兕犀混淆的端倪,两汉兕逐渐“犀化”,至晋以后定型。“‘兕’曾在数千年前广泛分布于华北,于春秋以后逐渐减少终致灭绝,其名逐渐用于长江流域类似的水牛属动物。汉以后此袭其旧名的‘兕’亦渐稀,于是逐渐转称独角犀。然而因与古籍所述扞格太多,故释者虽极力牵合仍多漏洞。”
笔者认为,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条件,使时人对兕的认知产生不同程度的差异,进而逐渐形成不同的动物学指涉,导致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兕名同而实异的现象。在兕名实之辨的问题上,从先秦至汉代,诸多文献中有犀兕并举的记述,《淮南子?南山经》:“祷过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犀兕多象”,姚宝猷考证祷过山在今广西;《左传?宣公二年》:“犀兕尚多”,孔颖达疏:“犀兕二兽并出南方”;《盐铁论?崇礼》:“夫犀象兕虎,南夷之所多也”。这些资料表明时至汉代,在南方地区兕应是一种与犀完全不同的动物,118号南越木简中的“兕”为牛属动物的可能性较大。
南越国的犀与牛
犀
野犀是陆栖大型动物,适宜在温暖湿润的森林、草地及河湖沼泽环境栖息。南越国各地区间的社会经济发展差异较大,除都城番禺发展水平接近中原地区,郡治所在地以及江河沿岸平原三角洲地区已有所开发外,境内的其余大部分地区仍保留着原始的生态环境。岭南地区是南越国的主要疆域,其地多山地丘陵,气候炎热湿润,植被茂盛,是我国历史时期野犀栖息最久,分布范围最广的地区之一。犀作为岭南地区的特产,史书多有记载。《史记?货殖列传》:“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汉书?地理志下》中亦有相似记述。《汉书?南粤传》:赵佗“谨北面因使者献白璧一双,翠鸟千,犀角十,紫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双,孔雀二双”。
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出土犀形璜是南越国犀牛形象的真实写照。这件犀形璜是南越王组玉佩的一个饰件,玉质坚致,呈黄白色,透雕犀形。头部有一大一小两个角,大角在额前,小角在鼻上。张口,塌脊如鞍状,中间钻一小圆孔,长尾下垂向上回卷,与头部呈对称状;前后肢蹲曲,蹄均三趾。器身中部浮雕涡纹。两侧有竖向的丝带痕迹。从外形上看,犀形璜的原型似为苏门答腊犀,江苏盱眙大云山汉墓中出土的鎏金铜犀牛的原型也是苏门答腊犀,其比例协调,通体鎏金,形象逼真,栩栩如生。苏门答腊犀又称双角犀,为犀类中最小者,肩高1.1—1.36米,身长2.5—2.8米,其最显着的特点是全身披着粗毛,毛为褐色或黑色,雌雄均具双角(雌性者前角高约150毫米,后角50毫米;雄性的角约比雌性长三倍)。苏门答腊犀是现代犀牛中最原始的一种,保留了许多祖先的特征,其多栖息于丘陵地的森林中,比较容易驯服。


南越王墓主棺室出土犀角形玉角杯,青玉质,半透明,仿犀角形,中空。《广州汉墓》中提到1134号、1153号两座南越国墓葬分别出土陶犀角15枚和4枚,其中1134号墓出土的陶犀角保存较好,呈青灰色或红黄色,仿犀角形,中空,大小相若,长17厘米,底径6厘米。该墓还出土1件绘犀牛的漆扁壶,外表髹黑漆,两面各以朱漆绘一犀牛,两侧及盖面绘菱形、扇形等图案花纹。犀角形玉角杯和陶犀角尺寸均与苏门答腊犀的前角接近,说明工匠制作玉角杯和陶犀角时是有实物参照的。这些文物皆可作为南越国时期岭南地区产犀的佐证。
牛
《汉书?地理志》记载粤地“亡马与虎,民有五畜,山多麈麖”,唐颜师古注五畜为:“牛、羊、豕、鸡、犬”。由此可知岭南地区在汉代已饲养家牛,南越国考古资料中亦有不少牛的形象。南越王墓东耳室出土4件带牛首形器耳的铜瓿,西耳室也出土有8件牛头形鎏金铜泡钉,位于广州农林东路的南越国墓葬86东林M3出土有8件带牛首形器耳的陶瓿。铜瓿和陶瓿上的牛首形器耳造型和刻划均较写意,仅塑造出牛首的轮廓,其中1件陶瓿的器耳保存最完整,牛脸瘦长,张口,额隆起,一对长角呈“Z”字形。牛头形鎏金铜泡钉造型和刻划则细致写实,牛大睁双目,额头正中有一尖锥形,并有三道凹凸横纹,表示皱褶。鼻孔上翻,双耳后面有长而后弯的牛角,头与角相接处有四道皱褶,并有一圈细小的刻划纹。牛头两腭下缘亦有细小的刻划纹,生动地呈现了岭南地区的牛形象。仅凭牛首我们难以断定这些牛首原型的品种,即使是南越王墓和南越国宫苑遗址出土了黄牛骨骼,也依然无法判定其为普通黄牛还是瘤牛。冯中源在《中国瘤牛》中提出虽然瘤牛和黄牛的外形明显不同,但它们在解剖学的骨骼结构上并无差异,仅在Y染色体结构上有微小的差异。

86东林M3中还出土一对陶牛俑。牛作站立平视前方状,双目圆瞪,口微微张开,神态憨厚,体型健硕丰满,四肢粗壮,肩有一个瘤状突起,颈部肉垂甚长,长尾夹于股间,双角双耳缺失,在相应位置各残留一圆洞。其肩部的瘤状突起、颈部长长的肉垂和健硕的体格都与云南滇文化青铜器上的瘤牛十分相似。瘤牛为黄牛的一种,因肩上的瘤状隆起而得名,亦称“峰牛”,其在《尔雅?释畜》中作“犦牛”,在《汉书?西域传》中作“封牛”。
瘤牛的祖先是印度野牛,吕鹏在《中国家牛起源和早期利用的动物考古学研究》中提出,瘤牛在我国境内最早出现于距今2400年的西南和岭南地区,现代瘤牛DNA研究和考古资料暗示中国家养瘤牛由印度及东南亚传入,云南很可能是中国最早引入瘤牛的地方。俞方洁在《滇文化瘤牛形象研究》中提出,结合印度、泰国的考古资料,瘤牛可能是从印度航至缅甸、泰国,通过怒江、澜沧江北上,抵达云南境内。从国内的考古资料来看,目前所知最早的瘤牛形象也是出现在云南江川李家山墓群出土的战国时期青铜器上,亦见于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出土的秦汉时期青铜器上,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李家山墓群出土的战国五牛青铜线盒和晋宁石寨山出土的西汉四牛骑士青铜贮贝器器盖上的立牛,瘤牛健壮丰肥,脊项上隆起高封,颈下肉垂甚长,两巨型角高高竖立,双目鼓圆,四肢并立,长尾夹于股间,形象生动写实。瘤牛的形象在广西地区战国秦汉时期的铜鼓上也有发现,贺州龙中岩洞墓出土的1件石寨山型铜鼓的鼓腰上装饰有8头瘤牛,公母相间。瘤牛抬首前视,四足并立,圆弯角,肩部有瘤状隆起,颈下有垂皮,长尾下垂。

云南、广西和广东同属百越民族文化区域,三省地域相连,珠江水系是三地交往的纽带。滇文化和越文化中有着像椎髻、纹身、跣足等相近的生活习俗,以及如干栏式建筑、铜鼓、提筒、羊角钮钟、羽人船形纹饰等相似的文化元素,足见两种文化交往之密切。目前,三地考古资料中的瘤牛形象,云南的时代最早且最丰富,广西次之,广东的最晚也最少。由此可推断,南越国时期广东地区的瘤牛是从云南经广西传入的。
(作者为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文博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