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曲锐
那一刻,汽笛为谁而鸣?
——音乐剧《斯文尼.陶德》漫谈
文/曲锐①
音乐剧
〔编者按〕本专栏将以“音乐剧”这一时下新颖热门的音乐戏剧题材为关注点,选取在欧美音乐剧市场中颇具代表性的6部作品进行解读,有从世界名着及畅销书改编而来的法语音乐剧《巴黎圣母院》《小王子》;有对中国观众而言,仅知歌曲《回忆》(memory),却不晓出自何处的着名百老汇音乐剧《猫》;有讲述了藏匿在巴黎歌剧院地下迷宫中的绝世天才的凄美爱情故事的《剧院魅影》;有用摇滚乐颠覆性演绎耶稣之死的先锋之作《耶稣基督超级巨星》;亦有主打惊悚、黑暗系的概念音乐剧《斯文尼·陶德》等。
针对上述所选定的剧目,遵循“冷热均匀”的合理调配,以“热剧普及”和“冷剧推广”为主诉求进行剧目筛选。前者即对中国观众有所耳闻的剧目进行全面、新颖的解读,加深读者对剧目的理解;后者所指的“冷剧”,仅针对中国的观众群体而言,碍于国内对欧美音乐剧普及度的欠缺,致使一些好剧、名剧在中国出现“国内冷、国外火”的特殊局面,因此将侧重从多元视角引入剧目,在加深观众对已知剧目的了解之外,更为观众提供了认识更多好剧名剧的平台。
2007年,由鬼才导演蒂姆·波顿(Tim Burton)执导,改编自同名百老汇音乐剧的电影《理发师陶德》(Sweeney Todd: The Demon Barber of Fleet Street))②出现在观众的视野之内,其大胆的选题内容即便在当时电影产业类型片多样化的环境下,以惊悚、恐怖、复仇作为故事背景线,以音乐作为叙事载体的音乐电影仍是比较冒险的尝试。
音乐剧《斯文尼·陶德》是斯蒂芬·约书亚·桑德海姆(Stephen Joshua Sondheim)制作的最为宏大的一部音乐剧,该剧虽然采用了传统的线性叙述模式和情节架构,但是在音乐上近乎歌剧风格的尝试对桑德海姆来说是一次很新鲜的挑战。然而,最特别之处在于该剧的主题选取了之前从未有人尝试过的血腥、黑暗的恐怖故事。桑德海姆用自己独特的音乐语汇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在故事情节之后所暗含的时代背景之下黑暗残忍的社会现实和苟延残喘在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众生相。
真实?虚构?
在现实世界中,“斯文尼·陶德”其人是否真实存在于世,众说纷纭。
正如蒂姆·波顿所言:“不知道它是真实还是虚构的,恰恰是这个故事的魅力所在;真的?假的?半真半假?恰恰是这个故事的矛盾所在。”那幺,关于“斯文尼·陶德”这个人物的原型到底出自何处何人仍然有着众多不同说法。就连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他的小说《马丁·翟述伟》(Martin Chuzzlewit,1843)中也曾提及魔鬼理发师,他在小说中劝告读者不要到伦敦阴暗的街头巷尾,因为有可能被做成人肉馅饼。
关于这位住在舰队街的恶魔理发师的故事,其实早在电锯杀人狂、鬼王弗莱迪等故事出现之前便已经成为英国家庭里大人吓唬小孩子的一种惯用说法:“被陶德抓走做成馅饼……”实际上,在小说、童话、戏剧等各文学领域中这类关于“吃人”的故事还是比较常见的,像姜饼屋的女巫、杰克与豌豆、小红帽等等,创作者们利用并将这种恐惧融进故事中,使读者们产生对于人吃人的恐惧心理。在19世纪早期,即维多利亚时代的初期,哥特式的恐怖血腥小说正在英国盛行,在这个年代,文学爱好者们用杀人狂魔的惊悚、恐怖故事取代了莎士比亚式的浪漫情怀剧,这种风气被认为是维多利亚时代最为显着的特征。这种对于血腥恐怖故事的偏好,似乎是想要借此表达由于城市化、工业化以及大都市生活变化给民众所带来的内心恐惧与不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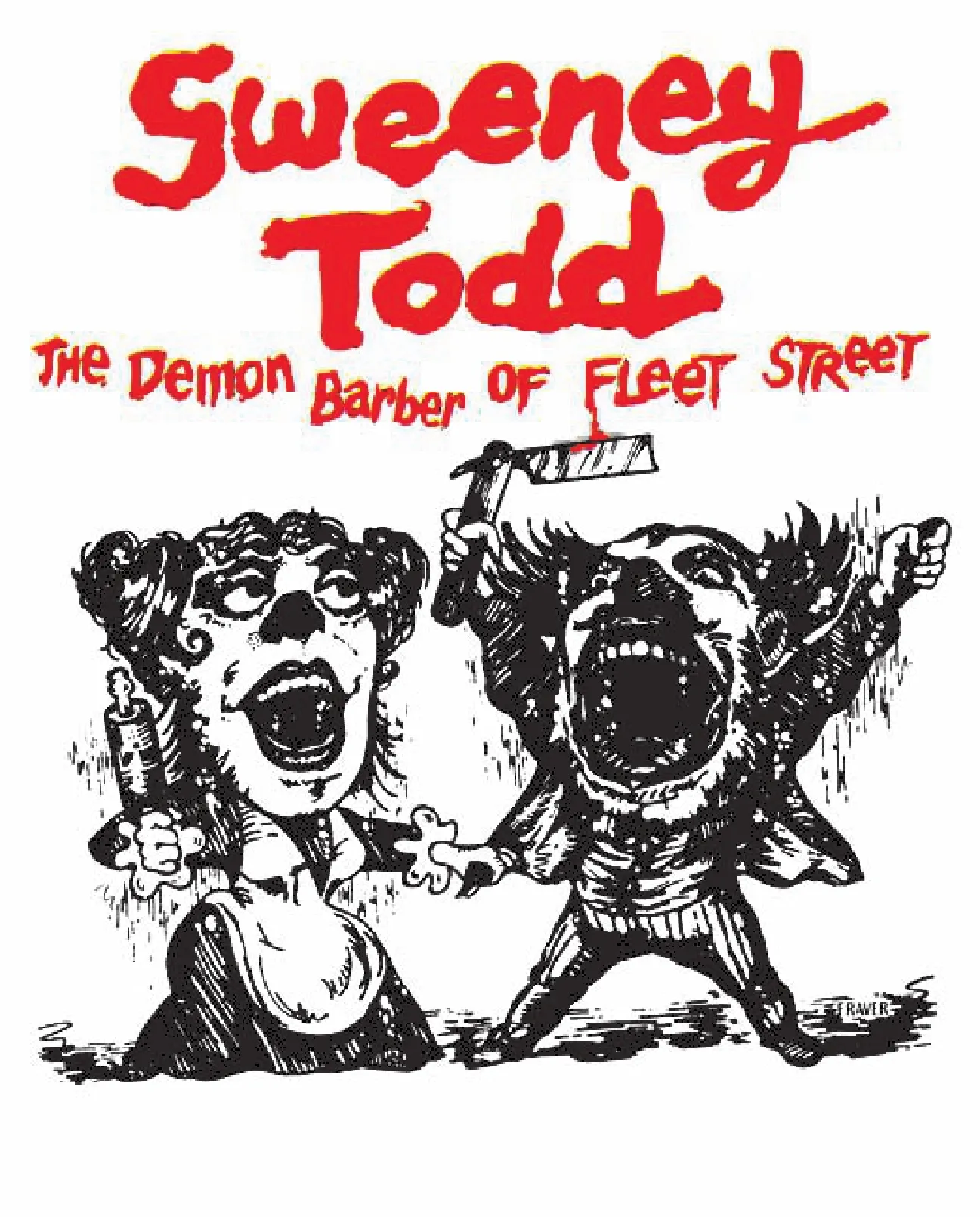
这个时代是英国工业革命的鼎盛时期,也是大英帝国经济文化的全盛时期。然而在富庶的表面下隐藏的是深深的贫富差距。在维多利亚时代,财富的分配始终不均,贫富对比十分明显。一方面是工厂主舒适的生活享受;另一方面则是失业工人绝望的生存挣扎。工业革命的后遗症使英国社会在率先迈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同时,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犯罪问题日益猖獗,以及各阶级之间贫富分化日益加剧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也随之应运而生。弱者越弱,强者越强,于是那些生存在资本主义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便极尽所能地扰乱社会治安用以报复社会。“斯文尼·陶德”便是被这一时期的残酷社会现实催生出来的悲剧人物之一。在音乐剧版中故事一开始,两个扛着尸袋的工人走上舞台,努力挖着坑想要将尸袋掩埋掉,挖掘的工人渐渐消失在坑口,警监出现并催促着工人,当一切都接近尾声时,突然耳边响起远处工厂传来的尖锐刺耳的汽笛长鸣声,故事正式拉开序幕。似在向观众暗示:这是一个充斥着黑暗和动荡的年代。


在斯蒂芬·桑德海姆的音乐剧《斯文尼·陶德》中,斯文尼·陶德被赋予了全新的定位。在这一版本里,陶德被冠上了凄惨的身世,他由原来纯粹的反面角色转变为有着凄惨过往、遭到不公正对待并背负着血海深仇的悲剧性角色。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独自一人艰辛地同命运抗争,但依旧被命运狠狠捉弄的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形象。
斯文尼·陶德就这样由一个毫无背景、邪恶的小丑式的小配角在桑德海姆的笔下转变为被资本主义社会欺压的底层悲剧小人物,邪恶的根源也发生了质的变化,由最初的主动性的邪恶转变成了被动性的邪恶,间接映射出了陶德所处时期的社会现状。
悲情小人物
1846年,伦敦,陶德再度踏上了阔别15年的故土。15年前的他,有着另一个鲜为人知的名字:本杰明·巴克,他原本拥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一位貌美如花的妻子露茜和尚在襁褓的爱女乔安娜。他们经营着一家理发店,一切都好似童话故事般那样幸福快乐。直到一天,邪恶的地区法官特平被露茜的美貌吸引,起了邪念。为了得到露茜,法官与执事共同谋划陷害陶德,最终将其流放至澳洲。
“陶德”这一角色的性格转变是整部剧中最具有悲剧色彩的。在历尽磨难的15年后,他以“斯文尼·陶德”这个名字回到家乡伦敦,陶德满心期盼,能够与自己的娇妻和爱女团聚。他相信,在他被流放的15年里,妻女是他内心最大的支柱和活下去的动力,此时他的动机是单纯且美好的。然而当陶德从邻居馅饼店老板娘洛维特夫人的口中得知妻子不堪凌辱服毒自杀、爱女被法官收为养女的双重噩耗时,陶德内心压抑了15年之久的对特平法官及执事的憎恨全部翻涌上来,陶德回归的最初目的被彻底逆转,就此走上了复仇的不归路。
就在陶德沉浸在噩耗的打击中无法自拔时,馅饼店老板洛维特夫人交到陶德手上一样东西,他的老朋友们:整套镶银剃刀。洛维特夫人提醒陶德这不仅是他赖以谋生的工具,而且是实施复仇计划的最佳途径。在歌曲“我的朋友们”(My Friends)中,陶德一边爱抚着剃刀一边唱道:“这些年你被锁了起来,就像我一样,我的朋友……回家了,我们又在一起了……很快你将会滴下珍贵如红宝石般的鲜血……我的右臂又完整地回来啦!”陶德将剃刀比作了自己多年未见的朋友,这里所谓的“朋友”是以复仇为共同目标的盟友关系,对之前曾是一名理发师的陶德来说,剃刀是他的谋生工具和左膀右臂。当洛维特夫人将剃刀再次交到他手上时,他身体中复仇的躯干终得完整。
为了让陶德在舰队街打响名号,洛维特夫人带陶德来到广场中央与另一位理发师皮莱利切磋技艺,陶德高超的刮面技艺成功引起了执事的关注。赛后某一天,特平法官准备向养女乔安娜求婚,为了让自己在最佳状态下进行求婚,便在执事的引荐之下光临了陶德的理发店。这本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复仇良机,却在关键时刻被一位鲁莽闯入的青年安东尼破坏,并且特平法官从这个青年口中得知乔安娜打算同这个青年私奔的消息后勃然大怒,痛斥陶德并扬言再不会踏入理发店后便愤然离去。
陶德初次的复仇之火被青年安东尼的一盆冷水浇灭了,也恰恰是这一盆冷水,浇熄了陶德内心所残剩的那点人性,他正式的沦为了一名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杀人恶魔
上文中我们看到特平法官来到陶德的理发店修面,在此之前,陶德理发店内的储物箱里已经藏匿了一具尸体,而他就是广场上与陶德切磋的理发师皮莱利。就在两人比试技艺时,皮莱利意外识破了陶德是本杰明·巴克的真实身份。原因是皮莱利之前曾在陶德的理发店做过学徒,对陶德的那套镶银剃刀记忆犹新。因此皮莱利得意洋洋地领着助手拉吉来到理发店试图以此要挟恐吓陶德,却不幸在陶德剃刀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接下来的一首歌曲“一个小牧师”(A Little Priest)里,陶德和洛维特夫人同谋将在理发店被陶德杀害的理发师皮莱利做成人肉馅饼以毁尸灭迹,如此一来便可长期地进行循环作案。只要有顾客上门理发、修面,陶德便将其杀害,尸体交由洛维特夫人加工烹制成各式美味的馅饼,馅饼的名称便以顾客的身份和职业来进行区分。 他们得意于自己想出的这个“妙计”,并乐不思蜀地幻想着各种“口味”的馅饼在店铺中出售。
此刻的陶德,从有目的性地向特平法官和执事复仇转变为向所有人复仇,陶德也成功地变身成为一台杀人机器。一台机器是不会有理智和感情存在的,这里陶德的精神已然崩溃,他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疯子。
惩罚?救赎?
除了在上述几段的描述中提及与陶德的复仇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角色之外,还有一位角色,她在全剧出场次数寥寥无几,观众甚至很可能不会记住她的身影,但她却可以说是促使这整部复仇悲剧发生的根源,她就是女乞丐。
纵观全剧女乞丐为数不多的几次出场来看,从陶德再次踏上伦敦的土地时,突然从黑暗处窜出的女乞丐疯癫的指着陶德说出:“等等…嗨,我认识你吗,先生?”到在散发着恶臭浓烟的馅饼店周围徘徊低语:“烟!烟!魔鬼的信号!”等等,她始终是作为起到警示作用的角色出现在舞台上。她始终在舞台的黑暗处小心翼翼地暗示观众,有些事情并非是他们眼睛所看到的那样,当洛维特夫人说出陶德妻子已死时那逃避的神态和眼神时;当乔安娜在阳台唱出美妙动听的歌曲时;当人们疯狂涌进馅饼店品尝所谓的“美味馅饼”时;当她两次对着陶德说出:“嗨,我认识你吗,先生?”时,她的警示也仅仅变成了一个符号,无法阻挡住陶德复仇的脚步,就在陶德得知自己顺手杀掉的女乞丐就是自己的妻子露茜时,他彻底崩溃,仿佛他之前所做的一切都成了笑料。自杀,成了他最好且唯一的救赎。也就在那一刻,远处工厂那尖锐刺耳的汽笛声再次响彻全场。
陶德是恶人?他也仅仅是在坚守着自己那残破不堪的“信念”,哪怕直到最后一刻,才被告知:上帝只是和你开了一个玩笑!信念瞬间被击碎,陶德该找谁申诉;陶德是好人?他十恶不赦、杀人无数,也杀掉了自己的良知和人性,这样的陶德又该找谁忏悔?剧终了,陶德用自杀来为自己犯下的种种罪孽赎罪。陶德是全剧中唯一一位数次徘徊在邪恶、良知边缘的角色,在陶德邪恶凶残的表象之下,呈现给观众的是内心深深的苦痛和绝望,只能靠着仇恨和杀戮释放内心的绝望,这也可能就是观众为何在走出剧场之后也无法去憎恨他的原因之一吧!
(附注:本文受“2013-2014年上海市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大文科研究生学术新人培育计划”资助)
曲锐(1985- ),女,上海音乐学院2012级戏剧理论研究方向博士研究生在读。
②该剧完整译名为《斯文尼·陶德:舰队街的恶魔理发师》,但限于其篇幅过长,笔者在遵循直译原则的基础之上,简化为《斯文尼·陶德》代指音乐剧版;音乐剧电影版名称则沿用广为大众熟知的《理发师陶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