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星,宋振国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天津市肿瘤防治重点实验室/天津市恶性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麻醉科,天津300060 )
乳腺癌是目前影响广大女性健康的重大疾病之一,且在中国广大女性乳腺癌的发病率一直居高不下[1]。外科手术是目前治疗早期乳腺癌的主要手段,但有研究发现手术期间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会使患者的机体免疫功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不利于患者的预后和康复[2]。麻醉用药和麻醉方式对于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一直受到医疗工作者的关注,不同的麻醉药物对患者的免疫功能则有不同的影响[3]。但是这方面的研究尚不多,在各方面持续努力评估麻醉的安全性是必须。本研究通过对丙泊酚、异氟烷、七氟烷3种麻醉用药对乳腺癌患者术前术后氧化应激和炎性作用影响的研究,分析哪种麻醉方式更有利于保护患者的机体免疫功能,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2015年5月1日至2016年5月31日本院接受乳腺癌根治术的患者60例,按照麻醉药物的不同分为3组,丙泊酚组(A组)、异氟烷组(B组)和七氟烷组(C组),每组20例。每组患者分别采用不同的麻醉方式来对患者进行乳腺癌根治术[4-5]。两种患者在治疗前均无放化疗、内分泌疾病病史,无高血压、心脏病等心血管疾病史,亦没有麻醉手术史,且3组患者在年龄上、性别上均没有明显的差异,具有可比性。本研究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2麻醉方法 A组:采用丙泊酚靶控输注(TCI)+持续泵注瑞芬太尼;B组:异氟烷吸入+持续泵入瑞芬太尼;C组:七氟烷吸入+持续泵入瑞芬太尼。麻醉维持:A组采用TCI泵入丙泊酚2~4 μg/mL,B、C组采用吸入异氟烷或七氟烷1.0~2.0最低肺泡有效浓度(MAC),3组同时联合瑞芬太尼(TCI泵注2~4 μg/L),调节麻醉深度维持脑电双频指数(BIS)值在40~60[6]。分别于麻醉前(T0)、手术切皮时(T1)、手术结束时(T2)记录患者心率(HR)和平均动脉压(MAP),并于T0、术后6 h(T3)、24 h(T4)、48 h(T5)、抽取静脉血样5 mL,即刻送检验科分离血清,应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Genzyme公司,美国)按照操作指南测定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IL)-6、IL-8、IL-10、IL-1β的浓度,应用硫代巴比妥法检测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过氧化氢酶(CAT)、谷胱甘肽(GSH)和丙二醛 (MDA)的活性[7]。

2 结 果
2.13组患者不同时期HR和MAP比较 C组的患者HR、MAP在T1和T2时高于A、B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他数据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3组患者不同时期的氧化应激类指标比较 SOD、GSH-Px、CAT、GSH与MDA的活性术前无差异(P>0.05),但术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T3和T4时,3组患者的SOD、GSH-Px、CAT、GSH和MDA浓度和活性与T0相比下降(P<0.05)。T5时,以上指标均明显上升超过T3、T4(P<0.05),且T5时,A组的升高幅度要高于B、C组(P<0.05),T5时MDA的升高幅度A组低于B、C组(P<0.05),见表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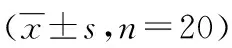
表1 3组患者不同时期HR和MAP情况
a:P<0.05,与C组相比
2.33组患者不同时期的炎性指标比较 血清TNF-α、IL-6、IL-8、IL-10和IL-1β等指标浓度出现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一氧化氮(NO)以及一氧化氮合酶(NOS)两种指标则出现了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与T0相比,T3、T4、T5患者血清CRP、TNF-α、IL-6、IL-8、IL-1β和IL-10浓度均升高(P<0.05);A组患者T3、T4、T5时点的CRP、TNF-α、IL-6、IL-8、IL-1β浓度升高幅度小于B、C组(P<0.05),但IL-10浓度升高幅度大于B、C组(P<0.05),T3、T4、T5时段NO、NOS与T0相比降低(P<0.05),T5时段A组上升幅度大于B、C组(P<0.05),见表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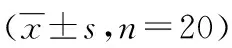
表2 3组患者不同时期抗氧化酶类指标比较
a:P<0.05,与T0比较;b:P<0.05,与T3、T4比较;c:P<0.05,与A组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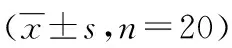
表3 3组患者在不同时期炎性指标浓度变化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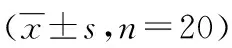
续表3 3组患者在不同时期炎性指标浓度变化情况
a:P<0.05,与T0比较;b:P<0.05,与A组比较
3 讨 论
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之一,有研究报道其可以占到女性癌症总数的15%以上,且以每年3%的速度在不断增长,严重威胁到广大女性的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8]。乳腺癌患者前期的治疗手段主要是通过外科手术进行根治,但是手术期间的麻醉方法都会对患者的氧化应激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9]。手术应激被公认为是围术期氧化应激的主要原因之一[10]。以往也有不少麻醉药物对人体氧化应激的研究,但鲜有不同麻醉药物和方法对患者氧化应激和炎性作用的研究。本研究就是通过研究3种不同的麻醉方式对乳腺癌患者氧化应激和炎性作用影响的研究来分析哪种麻醉方式更有益于乳腺癌根治术患者。
SOD、CAT和GSH-Px 作为生物保护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对抗脂质过氧化和细胞缺血后产生的自由基所造成损害的重要因子。SOD是自由基的重要清除酶之一,是抗氧化应激酶,其活性可反映机体清除氧自由基的能力。SOD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做是组织细胞所承受氧化应激能力的标志物,SOD活力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组织细胞中自由基的水平。GSH-Px对保护细胞膜的稳定性起着重要作用,是氧化应激反应中主要的防御物质之一,另一方面,GSH-Px在对抗细胞内包括氧化性应激在内的各种伤害性刺激方面起重要作用,这几种酶类的升高代表机体抗氧化应激的能力。MDA是脂质过氧化反应的主要降解产物,测定MDA可直接反映自由基水平。丙泊酚可能有效的抑制脂质过氧化,减轻损伤。丙泊酚的保护作用可能不仅仅是通过提高抗氧化酶的活性,而主要是减少了自由基的生成,缓解了氧化应激的状态。
丙泊酚是一种常用的全身静脉麻醉药,具有麻醉迅速,持续时间较短,不良反应较少的特点,一直因具有良好的麻醉效果而被广泛应用[11]。异氟烷是一种吸入性全身麻醉药物,与丙泊酚不同的是,它在使用过程中会对分泌系统产生轻微的刺激,目前也是广泛应用于医学领域[12]。七氟烷在医学中的使用相对以上两种麻醉剂较少,因其应用于临床的时间相对较晚,并且产生不良反应的概率大于以上两种麻醉剂,但是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提高和药物的不断改良,七氟烷作为全身麻醉的药物已经大幅度被使用了[13]。以往的研究中很少有3种麻醉药物对乳腺癌患者手术期间免疫功能的影响。同时对比3种药物对炎性因子如TNF-α、IL-6、IL-8、和IL-1β等指标浓度,发现3种药物都不同程度的抑制了以上因子的产生,对于抗炎性产生了较好的效果,这可能与异丙酚可以直接与氧自由基反应,生成稳定的2,6-二异丙基苯氧基团,抑制了氧化应激引发的级联反应有关。IL-10在天然免疫过程中是重要的抗炎因子,它抑制巨噬细胞分泌TNF、IL-1、IL-6 和趋化因子,有研究已证实, IL-10 可拮抗TNF、IL-1β等介导的促炎反应,并抑制细胞因子受体的表达及激活[14],但是炎性因子浓度还是要超过麻醉前的水平,因为麻醉药物的使用对人体免疫功能的损害是不可避免的。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PODKOWA等[15]的研究表明,使用异氟烷和七氟烷作为麻醉剂的患者在术后3 d IL-10和TNF-α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唐文志[16]的研究结果显示使用丙泊酚患的者术后CRP,IL-6水平与术前差异不明显。另外观察3组患者在术前和术后抗氧化应激酶类的水平,发现3组患者在术后SOD、GSH-Px、CAT、GSH、水平有所提高,且异氟烷的作用要强于丙泊酚和七氟烷。但是李建华等[17]的研究表明,使用丙泊酚和异氟烷对患者术后GSH-Px、GSH产生了抑制作用。ERBAS等[18]对45例腹腔镜胆囊切除术研究, 虽然七氟醚和丙泊酚抗氧化因子麻醉后增加有统计学意义,而地氟烷麻醉后总氧化剂水平增加较术前更显着。本研究发现,丙泊酚的使用对患者血清中炎性细胞因子类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且其作用大于异氟烷和七氟烷,但是对于患者NO和NOS的产生也产生了抑制作用,损害了其对病毒细胞的清除,且不良反应大于以上两种药物。
综上所述,3种不同的麻醉药物对乳腺癌根治术患者手术前后抗氧化应激及炎性作用都有积极的影响,总体来讲丙泊酚的使用效果要大于异氟烷和七氟烷,是值得大力推广和使用的。
[1]中国女医师协会临床肿瘤专业委员会,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中国进展期乳腺癌共识指南(CABA 2015)[J].癌症进展,2015,13(3):223-233.
[2]王静慧,李丽杰,吴光珍,等.健康教育干预联合康复指导对肿瘤化疗者的影响观察及远期生存质量评价分析[J].中国肿瘤临床与康复,2013,20(11):1294-1296.
[3]银含素,陈海林.不同麻醉在乳腺癌根治术中的应用分析[J].医学理论与实践,2014,27(5):570-571.
[4]宋红蕾,陈慧暖,洪春霖,等.血清胸腺嘧啶核苷酶1癌胚抗原糖类抗原153与进展期乳腺癌化疗疗效预后的关系[J].中国肿瘤临床与康复,2015,22(6):675-677.
[5]吕鹏龙,李煜,张生彬,等.不同麻醉及镇痛方法对乳腺癌手术患者细胞应激反应相关激素水平的影响[J].中国冶金工业医学杂志,2014,31(4):381-383.
[6]刘芳.二种全麻维持方式对乳腺癌根治书后疼痛影响的比较[J].医学信息,2013,9(31):80-81.
[7]刘继鑫.喉罩通气在乳腺癌根治术麻醉中的应用效果[J].中国医药指南,2013,11(30):91-93.
[8]张剑辉,栾世超,周宪方,等.康复指导教育对乳腺癌患者术后生活质量的影响[J].中国肿瘤临床与康复,2015,22(6):737-739.
[9]COTTRELL E B,CHOUR,WASSON N,et al.Reducing risk for mother-to-infant transmission of hepatitis C virus:a systematic review for the U.S.preventive services task force[J].Ann Intern Med,2013,158(2):109-113.
[10]马沛.乳腺癌根治术临床体会[J].中国实用医药,2013,8(10):103-104.
[11]李春霞.气管插管与喉罩麻醉在乳腺癌术中的效果及安全性[J].实用癌症杂志, 2014,29(1):88-90.
[12]JASSIM G A,WHITFORD D L.Understanding the experiences and quality of life issues of Bahraini women with breast cancer[J].Soc Sci Med,2014,107(1):189-195.
[13]JAFARI N,FARAJZADEGAN Z,ZAMANI A,et al.Spiritual well-being and quality of life in Iranian women with breast cancer undergoing radiation therapy[J].Support Care Cancer,2013,21(5):1219-1225.
[14]WANG Q,TANG X N,YENARI M A,et al.The inflammatory response in stroke[J].Neuroimmunol,2007,184(1):53-54.
[15]PODKOWA N,KOMASINSKA P,ROSZAK M,et al.Health behaviors among women diagnosed with breast tumours[J]. Pol Merkur Lekarski,2014,37(219):153-158.
[16]唐文志.瑞芬太尼在乳腺癌手术患者硬膜外麻醉时的辅助应用价值[J].实用癌症杂志,2014,29( 6):719-721.
[17]李建华,胡惠英,李斌,等.帕瑞昔布钠对乳腺癌根治术后布托啡诺病人自控静脉镇痛时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J].中华麻醉学杂志,2013,33(7):848-850.
[18]ERBAS M,DEMIRARAN Y,YILDIRIM H A,et al.Comparison of effects on the oxidant/antioxidant system of sevoflurane,desflurane and propofol infusion during general anesthesia[J].Rev Bras Anestesiol,2014,65(1):68-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