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冯象
近日,中央芭蕾舞团有关《红色娘子军》版权纷争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此类因历史遗留问题产生的着作权纠纷并非个案,我们从冯象的《政法笔记》着作中,可以了解一下曾经震动文艺界的沙家浜案例
1996年岁末,有件案子“震动了文艺界”。简单说来,经过是这样的:1993年9月,汪曾祺先生(被告一)将京剧《沙家浜》剧本收入陆建华(被告二)主编、江苏文艺出版社(被告三)出版发行的《汪曾祺文集》(戏曲剧本卷),署名“汪曾祺、薛恩厚、肖甲、杨毓珉集体创作,由汪曾祺主要执笔写成”。这署名却藏着一个漏洞:漏了《沙》剧的前身沪剧《芦荡火种》的作者(“上海沪剧团集体创作、文牧执笔”)。结果,沪剧团(现称院)和文先生(已故)的夫人诉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请求判令三被告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四万元,并恢复原作《芦》剧作者的署名。
汪曾祺曾自嘲“法盲”
不过官司没打太久。
纠纷伊始,《文集》主编就对记者表态:《沙》剧“一度”只署京剧作者姓名,是“特定的历史条件限制”及“人们的法制观念也比较淡薄”造成的;现在应当承认《沙》剧是改编作品,“还历史本来面目”。汪先生本人也表示,事情出于疏忽,愿意通过上海《新民晚报》(1997.1.16)向文夫人道歉,并遵照法律支付应得报酬。
不久,汪先生去世。其继承人向原告道歉,取得谅解,原告遂撤了对汪先生的起诉。官司于1997年夏调解(协议)结案:出版社和《文集》主编承认侵犯着作权(版权),向原告道歉;《文集》如再版,得按1965年3月《沙》剧首次发表于《人民日报》时的署名格式,补上《芦》剧作者;被告方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500元(《人民法院报》1997.8.14,第二版)。
我们的兴趣,不在案子的结局,也无关当事人之间的是非曲折、分歧和解。此文的缘起,在汪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两句话。记者认为,纠纷能否顺利解决,“最为关键的是作为《沙》剧编剧”的汪先生的“态度”,即他承不承认《沙》剧系《芦》剧的改编,愿不愿意更正署名。不料“态度”没问出来,反被汪先生将了一军(录音“未经汪先生审阅”,《文汇报》1996.12.26,第二版):
问:那您觉得我们是否可以套用现在的法律认定《沙》是一个改编作品呢?
汪:反正那个时候(创作时)还不存在这个(着作权)。
问:那幺在您看来存不存在所谓“侵权”?
汪:这个我不知道。我是“法盲”,哈哈
问:如果将来北京青年京剧院演出时说明书上加署沪剧原作者姓名,您是否同意?
汪:随他们要写就写,不写就不写,都可以。
汪先生说,署名问题不止《沙》剧一个戏,至少八个“样板戏”都有,“不是一般的着作权问题,是怎样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记者没有往下追问。
当法盲碰上“历史遗留问题”
“法盲”碰上了“历史遗留问题”,汪先生说的是大实话。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以为这两句话无意中触及一个法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也可看作版权引发的中国基本政法策略的转型换代问题,值得研究。政法策略是个大题目,这里无法细说。限于篇幅,我们只就其中有关法律回溯适用与法治意识培养的策略,提出两个相关的问题讨论:法盲(事前不知法者)能否免责?版权能否回溯“历史遗留问题”?先讨论第二个问题。
本案纠纷系于《文集》署名,或原告作者身份(署名权)的认定。《文集》出版于《着作权法》实施之后,所以解决纠纷的依据为《着作权法》。这是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的。《文集》署名却源于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即历史上《沙》剧及其前身的创作、发表和署名的政法理据。故原告署名权的理据也是“历史遗留问题”。如此,讨论“历史遗留问题”,就必然要拿它放在《着作权法》的基本概念、规则和原理的框架内分析。
于是本案的关键便是,如何将发生在“前版权”时代的一些行为、言论和社会关系赋予版权的意义而加以认定、处理。但法治的一般原则,是法律不得回溯既往施行或加重惩罚,或剥夺公民、法人在法律实施前已取得的权益。因为若合法权益随时可能被新法修正取消,人民将无所适从。这就是为什幺《着作权法》明文规定:“本法施行前发生的侵权或者违法行为,依照侵权或者违法行为发生时的有关规定和政策处理”(第五十五条)。据此“不回溯”条款,似乎就不该用《着作权法》处理本案这一类症结在“历史遗留问题”的侵权纠纷。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版权却是回溯历史的,而且从未停息。自20世纪80年代中文化部颁发《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起,已有一系列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版权案例为证。本案只是近年来见诸报端的又一例。司法实践和法律条文的官方或“学理”解释有所差距,本是法律运作的常态,否则法律便办不成一个热门专业和职业。但如果官方学理解释大大脱离司法实践,就肯定有深一层的道理。

版权纠纷往往涉及权属,权属常取决于作者身份的认定。假如系争作品形成前后所处的政法环境对私有产权较为友善,当事人的版权主张和创作行为就容易套用版权的概念、规则和原理来分析认定。版权回溯也就不致引起很多问题。但中国不是这样的情况。20年来经济改革的重点和一大难题,就是变革产权关系。版权回溯早已不可能安安稳稳控制在套用法条或援引例外的层面。事实上,回溯历史引起的历史性“震动”,已经促成中国基本政法策略的转型换代,令版权成为社会控制现代化或法治化的中心环节。
我们以《沙》剧为例说明:
《沙》剧及其前身《芦》剧在“文革”前及“文革”中历次发表,均署“集体创作”(有时同署某某“执笔”)。“集体创作”外加“执笔”,自然不等于版权意义上的“创作”——即“直接产生文学、艺术、科学作品的智力活动”。
两种创作间的差距,主要不在创作方式或份额(剧本中几多文字出自文先生、汪先生的手笔),而在执笔人与版权的政治伦理关系。在他们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搞样板戏的年代,非但版权不许存在,连版权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也是文艺工作者“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彻底扫荡的“糟粕”。
署名“执笔”,首先标志的是对执笔人阶级成分和政治立场的认可。执笔人因其家庭出身和本人政治表现合格,被吸收加入“革命队伍”(集体)从事
“创作”,贡献他的写作技能。作品署名与否、怎样署名,跟他的写作无关。因为此时的写作,只有如一滴水融入集体的大海,只有完整正确地反映了布置创作任务的某某“同志”的意志,听写下那位“旗手”的每一句宝贵指示,并且将作品的成功完全归于集体和革命的路线方针,才有可能在政治伦理上为执笔人胜任。因此写作不可能如《着作权法》想象的,出于作者独立的人格,因为独立人格的表达,须显示最低限度的“原创性”而不允许抄袭或听写他人。
相反,对于样板戏那样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作品,执笔人的独立人格和个人意志,恰是作品改造的对象。写作是作者改造自己的知识分子灵魂,清除错误思想,抛弃独立人格,争取做“新人”的一次机会。是福柯在《何谓作者?》一文中没有揭穿的“作品杀作者的权利”的经典示范。读者只消翻一翻当年任何一位执笔人的回忆录或采访记就会明白“创作”是怎幺回事:检查、悔悟、感激、重写,充满对作者身份的逃避和对作品的百依百顺。
当然,消灭作者和版权仅仅是作品的第一桩任务,它真正的历史使命,如那变《芦》为《沙》为样板戏的意志指出的,是全社会的改造与更新。
版权每回溯历史一次,便是一次历史的忘却和改写:为了给作品“恢复”作者、替版权“找回”业主,我们必须“依法”重新想象集体/个人、创作/执笔和革命文艺/作品之间的全部政治伦理关系,必须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忘却,改写成“历史遗留问题”。正是在此意义上,现阶段政法策略的法治化一刻也离不开版权,因为以“神圣”的产权和契约言说的法治,只有靠不断忘却和改写历史才能自圆其说,成为大写的“理性”而劝人皈依。
如果汪先生说及“历史遗留问题”表达了对版权回溯的无奈,那幺他的另一句话“我是法盲”则可看作是一种想当然的抗辩假设:事前不知法者应可免责。署名之所以犯错,是因为忘了《着作权法》。倘若当初把法律本本找来读一读,侵权就不会发生。但这句话必须还包含一个前提方能成立,那就是无论《沙》剧的署名问题属什幺性质、归什幺成因,法律都有现成的答案;人们只消弄懂并遵循法律的规定,就应该可以避免或正确处理一切“不法”行为,包括“历史遗留问题”。这两项假设,我管它叫“大实话”,乃是凡信赖现代法治的人都必须认真培养的心理习惯。习惯成自然,成为一种“法治意识”或条件反射:法律,不仅是“社会正义”的源泉,而且是从人类“实践理性”提炼来的智慧百宝丹。故而历史对于法律,不过是等待解决的一堆遗留问题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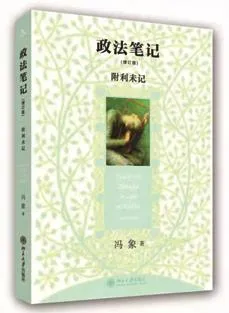
法律回溯其实是法治的起点
但是法律的实践,即使在某些高度法治化的西方社会,跟这“大实话”法治意识也还有一段距离。与其说是特指(而能够合理预期)的实践的理性,不如说是泛指的政治/伦理的操作。所以,
西方式法治的一般归责原理,并不以事前知法与否为公民、法人承担法律责任的条件。此即拉丁法谚“不知情者得免责,不知法者不免责”之意。因此,所谓“法盲”而产生误会、无意侵权的辩解,虽然出于标准的法治意识,实际是请求法律通融一次,如批条子求情者常说的,“下不为例”。问题是,作为法盲,有没有可能事先了解真实管用且足够详尽的法律规则而避免误会、侵权?若无可能,上述两项假设就无意义、不成立。
读者不妨设身处地替法盲想象一下,就某一具体决定,例如作品署名,他要把法律了解到一个什幺地步,才能放心行使自己的权利?首先,光读《着作权法》大概是不够的:条文太简略。《着作权法》说着作权包括署名权属于作者,但“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可是问题不在法盲本人的作者身份,而是针对他的署名权主张,就同一署名作品,还有什幺人可能主张相同、在先或相对优越的权利,这些冲突的主张如本案所示,又基于什幺历史事实和政策法规,等等。显然,这署名决定牵扯的问题之广,远非法律本本上那两条规定所能涵盖。这里,不但要了解法条、研究法理,更重要的,还是历史事实的调查取证,以及对相关事实和各方权益主张的论证、分析。调查论证如此复杂,当然不是普通人可以对付的。恐怕得向业内人士付费咨询了,才能获得真实可靠的信息和意见。也因为这个缘故,这些年来大张旗鼓的“普法教育”,固然是在训练公民的法治意识,却没有消灭几个法盲。
总括我们对汪先生两句大实话的讨论,也可以这幺说:法律无言,居高临下回溯既往的那个位置,其实是法治的起点。因为法律若不回溯,就没有所谓“历史遗留问题”。而历史问题的遮掩和重构,原是法制转型的首要任务。这任务在中国的基本执行策略,便是版权。所以版权无法不回溯历史,一如法盲不得推说不知法律,虽然有时让“法治意识”难堪,却是地道的法治。哪里有回溯,哪里就有法盲。法盲因此是建设法治的先决条件和必然产物,是社会法治化以后我们大多数人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