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帮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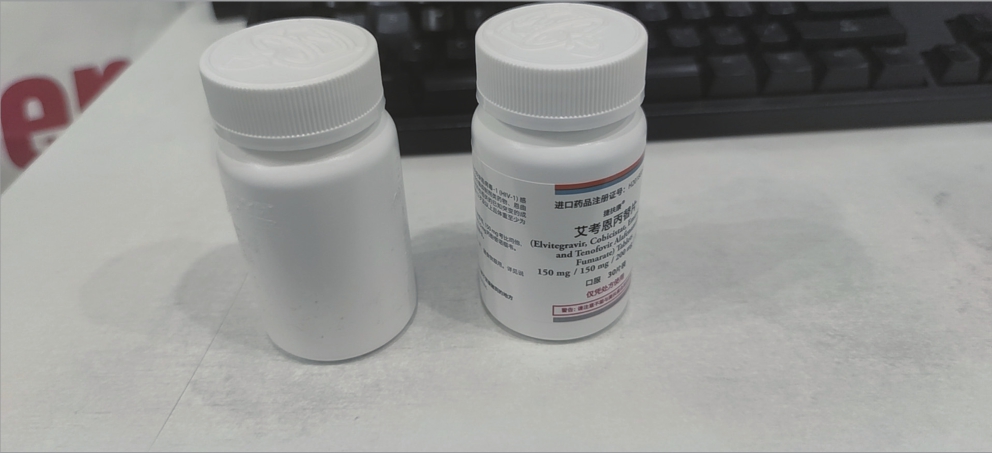
40年,足够科学家们在其他行业大谈理想、大显身手,但面对艾滋病,我们只能通过终身服药的方式将其压制,不表现出来。这样的成果是快是慢,我们很难去做对比,因为艾滋病太特殊了,在它背后是狡猾的HIV病毒,而在社会上,它又难免让感染者受到误解甚至歧视,艾滋病人成为社会上一个特殊的群体。
感染者:日子还是要继续
小阴,男,29岁,目前在深圳工作。今年7月31日,小阴在公司的例行体检后接到了医院的电话。“电话打过来我就知道出事了,”小阴说,“刚开始的几天我还是挺不能接受的,一直在想我会不会就这样死掉,那几天压力特别大,头发一直掉,洗澡的时候一抓就是几十根。”描述的过程中小阴的语气很平静。“不过后来一想,这不就是吃药的事儿吗?世界那幺大,意外在不断的发生,我这只是其中一个意外而已。”小阴说自己两三天的过后就想通了这个问题,目前每天按时吃药,跟正常人一样。
小阴的病毒是他的伴侣传染的,确定关系之前,他们去做过一次检测。小阴回忆道:“可能是那次检测中没有专门的抗体检测,结束后医院并没有打电话过来告知任何异样。”而在今年4月份时,在一次高危行为后,小阴出现了一次长达15天的发烧,去了医院才治好,在那次之后他就隐约觉得不对劲儿了。回想起来,小阴觉得自己运气不好才会感染这种病:“在这个群体里,感染这种病是风险还是挺大,我知道我的病是他传染给我的,不过也不能怎幺样了,我们现在成了病友。”
目前,小阴每天一片艾考恩丙替片,药物一个月1290元,小阴一个人承担。“药物的钱对我倒是没什幺压力,我也并没有打算告诉自己的家人,因为告诉他们了无非也是吃药,我的这个状况只有一个发小知道。”
小王是贵阳人,2020年刚过完春节他前往珠海打工,之后与伴侣发生了高危行为。2月23日前后,小王出现了一些症状:发烧,没有力气,皮肤红疹。他买来HIV试纸一检测——弱阳性。随后再去医院检查,最终确诊。“我去医院检查结果是阳性,医生告诉我做好一系列的准备和治疗方案,我一个人异地他乡无依无靠,知道得了这种病,我很崩溃,很难受。”在确诊时,小王只有18岁。他说:“我打电话告诉我家里人我的状况,我们隔着屏幕一起痛哭”
回到贵阳,小王在贵阳五医“刘主任”的劝导下开始一步步走出面对生活。“第一次吃药的时候我跟妈妈抱在一起哭了,因为从那天开始吃药就是一辈子的事,它就是我的‘救命稻草,我每天都不敢忘记吃药。我也慢慢了解到HIV不是我想象中那幺恐怖,它就是一个病毒破坏人体免疫力细胞,只要你好好吃药,锻炼身体,那跟正常人没有什幺区别。”小王还告诉我,在开始治疗的这几个月里,社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经常打电话来关心,通过治疗和锻炼,自己的身体好多了,没有感冒也没有发烧过。

但在治疗中,小王还一度想过放弃,他说:“家里有个快结婚的哥哥和一个负债累累的家庭,现在这个药一个月1290元,我年纪太小,吃其他的药副作用很大,我不想家里付出那幺多。不过刘主任给我心里安慰,我也明白要好好活下去,身体健康就是家人最想看见的一面。”除了家人,小王还把感染的事儿告诉了自己要好的两三个小伙伴,他们都不介意。
今年12月初,中国国家卫健委最新消息显示,截至2019年10月底,中国报告存活艾滋病感染者95.8万例,这只是已知存活下来的,隐瞒不报的和因病而亡的只会更多。而在贵州,自1993年发现首例病例以来,目前累计检测出的感染者为6.8万,现存感染者4.6万。
艾滋40年
1981年6月,美国的一篇周刊上介绍了5例艾滋病人的病史,这是艾滋病在世界上第一次有了正式记载。一年后,科学家正式给他命名——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有人推测,在艾滋病被正式发现并确认前,已有10-30万人感染了。
艾滋病怎幺来的?最受认可的说法是,在非洲喀麦隆南部灵长类动物身上带着与HIV极为相似的病毒SIV(猴免疫缺陷病毒)而当地人有捕食黑猩猩的习惯,在捕杀过程中,如果刚好接触到感染了病毒的SIV,病毒就会通过血液进入到猎人的伤口,使人类感染,并通过适应人体演变成HIV。
在艾滋被正式确认到往后的六年里,科学家们对它束手无策,直到1987年,才出现了第一种对抗艾滋病的药物——核苷类反转录酶抑制剂,这种药物一直被使用至今。不过HIV病毒在人体内会发生突变,光使用这一药物根本无法抑制病毒。被广泛认可并推广的治疗方式为鸡尾酒疗法(高效抗反转录病毒疗法),感染者需同时使用三种以上不同机理的药物联合抑制病毒,从而达到阻止病毒传播的效果。
近年来,在预制病毒的药物上,科学家们一直在努力。2006年,全球首个用于HIV感染完整治疗方案的口服单一片剂药物依非韦仑/恩曲他滨/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酯复方片获得美国FDA批准,革新了HIV的治疗,从每天吃一把药,变成了每天只需吃一片药。2018年,比克恩丙诺片问世,其结构结合了创新的不含激动剂的整合酶链转移抑制剂(INSTI)比克替拉韦,以及药物有效性和安全性均经过验证的双核苷反转录酶抑制剂骨干药物(NRTI)恩曲他滨/丙酚替诺福韦,具有强效的抗病毒疗效,较高的耐药屏障和已证实的良好的耐受性。
除了药物治疗的进步,艾滋病治疗的其他两个方向,“疫苗”和“基因疗法”却迟迟没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疫苗自研发后30多年来,全球开发的项目达40多个,进入临床试验多200多次,每年用于艾滋病疫苗研发的经费超过8亿美元,但绝大多数以失败告终。目前最受人关注的是美国强生旗下的一块叫“马赛克”的疫苗,该疫苗在2019年九月进行了千例人体试验,对猴子100%地出现抗体反应,且单次暴露于艾滋病病毒下感染风险减少了94%。有人认为这是迄今为止能抵御最多种艾滋病病毒毒株的“通用疫苗”。2020年7月世界艾滋病大会上,圣保罗联邦大学的Ricardo Diaz及其团队发布消息,一名36岁男子在接受了特别激进的药物治疗后“抗逆转录病毒(ARV)药物+烟酰胺(维生素B3)”,于2019年3月撤除了所有艾滋病毒治疗,直到2020年7月,在该位患者中没有检测到HIV病毒。简单来说,就是通过烟酰胺暴露潜伏性细胞,然后使用超级鸡尾酒疗法一举杀死所有病毒,不过跟这位圣保罗病人一起治疗的其他4名患者并没有达到同样的效果,在接受同样的治疗后,他们体内的HIV病毒迅速复发,其原因目前并不了解,但这种治疗方法目前还存在诸多争议,圣保罗病人体内的病毒是否彻底清除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观察。
基因疗法则更多的带给人们惊喜与意外,“柏林病人”和“伦敦病人”二人都是因为治疗其他疾病而进行了骨髓移植,最后都意外的发现清除了体内的HIV病毒。不幸的是,今年9月,“柏林病人”,也是第一位被治愈的艾滋病人白血病复发去世,享年54岁。而发生在这两位病人身上的治愈手段——骨髓移植——并没有受到推荐,原因是这样的治疗方式副作用太大了。今年5月外媒报道,德国汉堡的科学家正在使用新的基因与细胞疗法来对抗艾滋病。在汉堡生物技术初创公司Provirex的支持下,研究人员正在开发一种基于“基因剪刀”(gene scissors)的新疗法,从被感染细胞的基因组中“切出”HIV的原病毒,并消除该病毒。如果能够临床成功,这将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体内彻底去除HIV病毒,而之前对艾滋病的治疗只是抑制该病毒的复制和繁殖。
突变:幽灵般“复阳”的罪魁祸首
HIV病毒进入人体后开始攻击人体的CD4细胞,病毒本身是RNA病毒,开始潜伏人体后便会“自带”工具酶进行逆转录(从RNA变为DNA),DNA潜进宿主细胞核,便永久性地插入到人体染色体中,随后大量消耗细胞内的营养物质,大量生产病毒颗粒,直至宿主细胞枯竭。一开始,科学家认为只要抑制它的逆转录酶,不让它逆转录为DNA进入细胞基因组,关键一环,就能把HIV切断。然而不料病毒一定时期组织形成自己的病毒库,它掌握了人体内哪个细胞是“卧底”,哪个细胞是“敌人”,体内的免疫细胞都成为了“人质”,让药物找不到靶子(逆转录酶),这就是耐药。耐药的出现,让艾滋病疫苗的诞生也变得渺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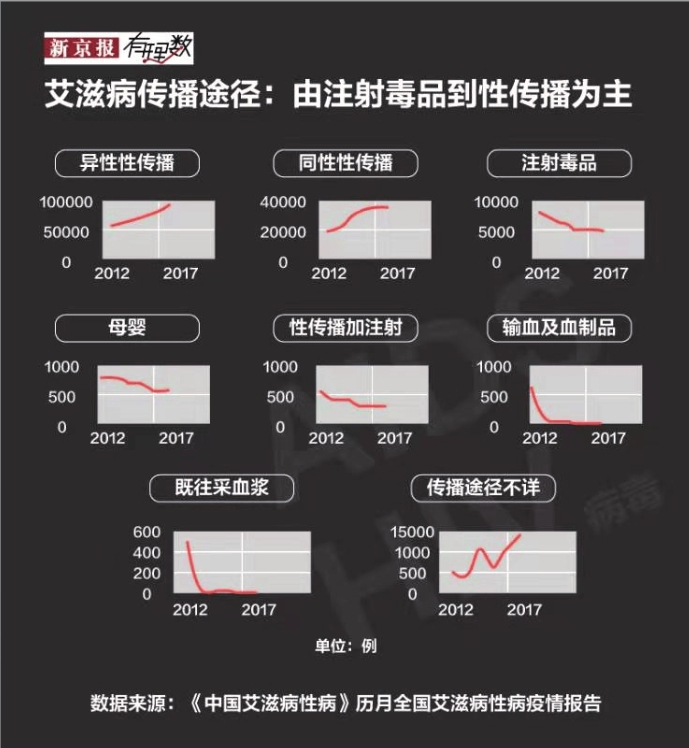
2019年,我国制定的《遏制艾滋病传播的实施方案》中,将防治工作分给了更多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贵州省在今年10月31日前,已设立了106家抗病毒治疗定点医院,覆盖全省所有市(州)和88个县。“十三五”期间,抗病毒治疗覆盖率接近90%。
我们还不确定最后最后杀死艾滋病毒的最终会是谁,它可能是一种先进的生物技术,也可以是某种有效的治疗手段或是一种特效的药物。但我们可以肯定,战胜传染病的,一定是我们人类自己,不光是预防和控制策划,还有我们对病毒的认知和对感染者的关爱。
(编辑/张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