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仁文
2004年,我在耶鲁大学,其时正赶上中国近代留学生之父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150周年。当时的中国留学生会请我们几个国内去的访问学者一起参加一个座谈活动,我谈到一个感想:当年容闳来美国,在海上颠簸了98天,如今我们十几个小时就到了。但如果把人生看作一场旅行的话,谁能说我们抵达后的日子就一定比那船上的日子更有意义呢?钱锺书写《围城》,大量的细节来源于他和杨绛从法国坐船回中国的经历,如果以坐飞机的速度回到国内,只怕《围城》也就不是现在的《围城》了。
肉体的漂洋过海反倒不断促使自己的灵魂回到那个给我灵感的故乡山村。我小时候听父辈说,他们要去县城读个书,挑着行李要在路上走上几天,途中还要借住老乡家中。我上学时,虽然已经一天能往返于县城,但那时到北京来上学仍然要经过多方辗转,没有几天是到不了北京的。如今,一天内就能从北京轻轻松松抵达老家。交通的日益迅捷使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越来越成为地球村,康德当年所设想的国家之间的联邦制曾经被认为是遥不可及,但现在区域出现了欧盟这样的一体化组织,国际组织出现了联合国这样的机构。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日益形成,不管是康德所设想的“全球联邦”“世界公民”还是我国学者赵汀阳所设想的“世界政府”“全球公民”,一定会以某种方式加速出现,它所带来的对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冲击与重构也将考验着我们的想象力。
网络技术的日新月异更是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时空观,鼠标一点,再远也是顷刻之间。马克思曾经指出,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回看互联网诞生几十年来给世界带来的变化,其速度、影响恐怕要大大超过工业社会。我记得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听人说起以后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来投稿,还云里雾里,谁知短短20多年过去,现在我们连电子邮件都用得不多了,而是越来越多地使用微信。曾经,有人跟我描述未来我们靠一部手机就能走遍天下,当时我还难以想象其具体场景,但如今这一天已经到来,无论身处世界何处,一部手机,从导航、阅读到购物、转账,一应俱全。网络世界使远的变成近的,近的反成远的。法律是社会的反映,社会结构在巨变,社会的运行方式在巨变,它能不要求法律制度和法学理论作出相应的调整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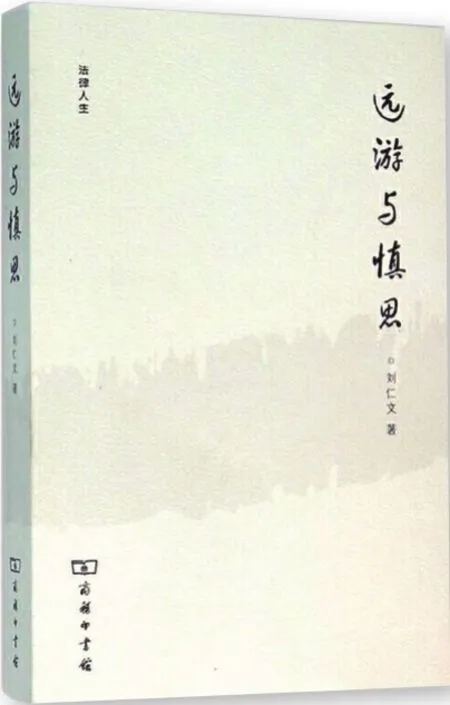
《远游与慎思》刘仁文 着商务印书馆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说的是学与思的互动。这句话同样可以用来说明游与思的关系,其实对于我们学人来说,游也是学(游学)。
40多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是中国有史以来广度和深度最大的一次睁眼看世界,毫无疑问它对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法治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一位美国法律界同行曾跟我感叹:在中国,很多法官都对英美法系、大陆法系有了解,相比而言,美国的法官可能对别国法律体系的了解就差远了。实事求是地说,我们过去都是带着学习的眼光去考察别国的立法、司法和法学教育的,而且对自己的专业思考也是很有帮助的。
但现在可能到了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了:“在借鉴了一切外来的知识之后,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或之后,世界也许会发问,以理论、思想和学术表现出来的对于世界的解说,什幺是你——中国的贡献?”2018年,我曾在日本东京参加过一个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和日本早稻田大学比较法研究所学术交流25周年的研讨会。当时中方代表团团长、法学所所长陈甦教授就提到,自己当年第一次出国就是来早稻田大学学习,那次学习对自己的学术生涯有重要影响,所学到的知识对自己回国后参加相关的立法活动也有很大帮助。现在的中国法学虽然已经摆脱了对外来知识的过分依赖,但这并不意味着比较(法)的不重要,相反,恰恰是知识互惠的开始。对此,日方的楜泽能生教授回应道,比较法以“知他而知己”为目的,只有通过比较才能更好地了解自身。在全球化、可持续发展、区域共同体等语境下,“法的普遍性和民族性”将成为一个关键词,中日两国的法学交流与合作迎来了一个前景更为广阔的新时代。从过去的单一学习域外知识到如今的双向交流、互有所得,是我在许多国际会议上的一个共同感受,这给我们的观察和思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林达在《带一本书去巴黎》中说道:在巴黎,走一段读一段随身携带的雨果的《九三年》,才发现这本书不是30年前的年龄所能读懂的,必须再一次甚至不止一次地重读。不仅《九三年》如此,从巴黎回来之后,作者又去找出《双城记》《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在重读中找到新的感受。这样的体验我也有过。我们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似乎是分别强调这两件事的重要性。其实,二者本身有一种互相促进、互相升华的关系。因为要远游,所以带上几本与目的地相关的着作;又因为远游,回过头来想去读某些着作,远游带动了阅读、拓展了阅读、深化了阅读。
一般来说,法律人的游学既包括法学院的听课和授课、学术会议上的发言和交流,也包括去旁听法庭庭审、议会辩论,访问律师协会、宪法法院等法律机构,偶尔还有人文地理、历史风情的考察,所看所思会往返于专业之内和专业之外。有时远游结束了,甚至早已回到国内,但偶然一个联想、一缕记忆,又泛起对某一问题的思考,忍不住要顺藤摸瓜去阅读。
博登海默曾警告:“一个法律工作者如果不研究经济学与社会学,那幺他极容易成为一个社会公敌。”社会科学对法律人知识的重要性如此,人文科学亦不例外。怀特在《法律的想象》中就指出:“文学名着为法律的各种人文价值提供了良好的伦理描述。”行文至此,我们似乎就不难理解,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一则关于守门人不让一个求见法的公民进入法的门的文学寓言,竟能成为西方法哲学迄今无法绕开的主题,“所有西方哲学只不过是柏拉图的注脚;同样可以说,所有西方法律的论述不过是卡夫卡的注脚。”(怀特海)可见,对于今天的中国人而言,非法律人士要防止“读书万卷不读律”,法律人士则要防止“读律万卷不读书”。
“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在抗击新冠肺炎的特殊日子里,重温帕斯卡尔的这句话,更觉人的渺小与悲苦,也更感思想对于人的尊严的意义。病毒阻止了人们的远游,但阻止不了人们的思想,相信人类经此劫难,定会在思想上有新的收获。(《远游与慎思》,刘仁文着,商务印书馆2015年一版,2020年增订版。本文节选自《远游与慎思》增订版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