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国辉
薇拉·凯瑟(Willa Cather,1873—1947)在美国文学史上是一位着力描写美国中西部“拓荒时代”生活的伟大作家。同时,她又被称为“拓荒时代”的挽歌作者。挽歌是对无法挽回的往昔发出的追颂和悲叹,是对薇拉·凯瑟后期作品的准确概括。在小说《一个迷途的女人》中,以福瑞斯特太太的命运为主线,讲述了她随着时代改变而逐渐迷失方向,追溯印第安人的“失踪”,想象年轻一代的命运,如一曲完整的挽歌贯穿了整部作品,它不仅为伟大的“拓荒时代”而奏响,还隐含了作家内心的悲哀和迷茫。
印第安人——远去的一代
故事发生在丹佛市甜水河镇,这里原是印第安人的地盘。福瑞斯特上尉在宴请尼尔、艾林格及奥格顿一家的聚会上,谈起了往事。通过回忆,印第安人曾经的生活图景得以呈现:
“天天都是好天气,可以打猎,有许多羚羊和野牛,天空一望无际,阳光普照,草原也无边无垠,青草随风荡漾,长长的大湖,水流清澈,开遍了黄色的花朵,野牛换季迁移的时候到这里来喝水、洗澡,在水里翻滚。”
当时,年轻的上尉在一家运输公司当车夫,路过此地,他雄心壮志地感慨道:“这是年轻人理想的生活。”往南探路时,他发现甜水河有一处印第安人的营地,就在他们现在房子所在的山上。上尉一下子就喜欢上这个地方,决定将来要在这里盖幢房子。此后多年,上尉一直忙于建设铁路,肩上又有责任,但从未忘记这个梦想。终于有一天,他回来并买下这片土地。当看到曾经插下的柳枝已经长成了一棵树,上尉又种了三棵,标出房子的四角。十二年之后,上尉功成名就,带着年轻漂亮的太太回来盖了自己的房子——就是此刻聚会聊天的地方。
但问题是,曾经住在山头的印第安人哪儿去了呢?为什幺上尉可以从铁路公司买下这片土地,盖起自己的房子?上尉在他看中的地方插下柳枝意味着什幺?他何以如此雄心勃勃?
美国独立战争之后,为了适应经济发展和维护政局稳定,开始大规模的西进拓荒运动。面对散布在西部无垠草原上的印第安土着部落,政府采取了圈定保留地这样有失公允的措施,将印第安人迁到更为边远的地区;如有反抗,则遭到无情屠杀。政府强迫印第安人交出来的土地,或者搞开发建设,或者通过买卖等方式安排给拓荒者来居住和开垦。因此,上尉插下柳枝不禁让人联想到英国历史上的圈地运动,他的雄心不过是侵略者的强力罢了。

在故事的结尾,上尉讲到他的人生哲学:
“‘因为用像我说的那种方式向往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已经成为一个事实。我们所有伟大的西部就是从这种梦想里发展起来的,包括分到土地的移民,勘探的人和承包工程的人。我们梦想有横跨平原的铁路,像我似的,梦想在甜水镇定居。对于后代来说,这些事实都是司空见惯的东西,可是对我们来说——福瑞斯特上尉‘哼的一声结束了他这番话。他的语气里有一种可怕的东西,那是孤寂、挑战的调子,这种调子我们常常从年迈的印第安人口中听得到。”
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上尉那一代拓荒者“伟大的梦想”以及征服印第安人而开疆拓土的事实。但上尉最后“哼”的一声,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什幺呢?一是对年轻一代企图坐享其成的不满和愤慨;第二,有种骄傲自得的神气,回想起了当年打江山的豪情壮志;第三,如今的上尉却病痛缠身,处于夕阳西沉之时,他的愤慨同时也是无奈。最后一句提到了“年迈的印第安人的调子”——孤寂、挑战,同上尉的一模一样,事实上构成了对上尉一代人所谓“开拓者精神”的解构,原来,上尉们的疆土是从印第安人手里夺过来的。尽管作品对印第安人着墨不多,作家极力称颂的是“拓荒者精神”,但这里有意无意的补充叙述非常重要,透露出薇拉·凯瑟的人道主义精神,或者说是她对历史事实的正视。
此外,文章还有一处谈到印第安人。年轻的律师艾维·彼得斯帮忙代管福瑞斯特太太的业务,但他心术不正。福瑞斯特太太同尼尔谈到他时,急忙说道:“他想了什幺办法从印第安人那里弄到上好的田地,几乎不花什幺钱。别告诉你舅舅;我想他准是欺诈来的。”“我不赞赏那些欺诈印第安人的人。真的不赞赏!”她激烈地摇摇头。
印第安人成为上尉那一代驱逐的对象,他们的地盘被建成了如今的甜水镇,过往几乎没有留下什幺印记。现在,新一代的年轻人又投资更加偏远的怀俄明州,继续欺诈印第安人。福瑞斯特太太即便在感情上同情他们,然而,她所享受的生活、所拥有的地位哪一样不是开拓者们用印第安人的血泪换来的呢?过往是,现在是,一旦失去了这个支撑,福瑞斯特太太就成了“一个迷途的女人”。
福瑞斯特上尉——拓荒者的一代
“在这些大草原的州里有两种显着的社会阶层:一种是分得土地迁居来的和干手工活的,他们到这里来为的是谋生;另一种是银行家和办大农场的绅士,他们从大西洋岸边来,为的是投资,或者用他们常用的话说,为的是‘开发我们伟大的西部。”
福瑞斯特上尉属于后一种。经过几十年的打拼,他已经从一个年轻的车夫挤入上层阶级,还娶了一位漂亮的太太。他自己是铁路上的人,承包各种赚钱的生意。他的别墅——靠近铁路沿线的“福瑞斯特之家”,成为很多上层人士因生意往来途经甜水镇的歇息地。
江山已经打下,梦想变为现实。福瑞斯特同他的老朋友们正享受着这一切。拓荒时代为伟大梦想而奋斗的历程和他们这一辈人的英雄精神、贵族教养能够通过小说窥见很多。
福瑞斯特上尉“外表笨拙而有威严,内心深沉,从不做欺诈亏心的事情。他镇静自若,好比一座大山”。不管有什幺骚乱,只要把粗壮、厚实的手搭到闹事者身上,就能够使其平静下来,像平息一场狂乱的风暴。当他手拿威士忌,同朋友们祝酒时,说出的“干杯”两个字是那幺庄重而有分量,仿佛一个严峻的时刻,在敲响命运之门,以至于尼尔感到了“一阵快意的颤抖”。这是一种什幺样的力量呢?上尉——这个魁梧的人,作为开拓者,他英雄般的伟业凝聚成内心的精神力量,使他几乎成为一个精钢雕塑。
当全国性的金融危机来袭,福瑞斯特上尉的银行濒临倒闭时,为了偿还那些存钱的客户,他取出自己的私人保险箱,当众打开,将所有的票证放在桌上分类出售,还派人到市场上卖掉矿产股票和其他证券。上尉的善心和正直赢得了朋友们的赞赏。在生活中,福瑞斯特处处保持良好的教养。有朋友来家聚会,他会整整齐齐地穿着礼服大衣,系着硬领和黑色的领结,亲自在门口迎接。用餐时,客人要火鸡的任何一个部位,他都能连肉和塞在里边的东西和汤汁,切得整整齐齐递给你。如果他想要抽烟,就会挨个问每一个宾客,用的是同样的词语和语气,“我抽烟你讨厌吗?”可见他对每一位客人的尊重。
然而,时代正在发生变化,社会的发展并不会讲人情。随着西部开发的黄金时代结束,资本主义势力迅速崛起,新的阶层慢慢侵蚀和取代了拓荒者一代。上尉生意破产,银行倒闭,老朋友们很少再来探望他。同时,美国社会的日益商业化和随之而来的道德堕落也如疾风骤雨一般向他扑来,一双双势利的、邪恶的眼睛紧盯着他的土地、他的房子和他的太太,这种强势和贪婪当然不是福瑞斯特上尉所能阻挡。美好的创造性时代即将终了,不祥的的新时代正在开启。道德高尚者退出历史舞台,而卑劣者成为新的主人。
作者所讴歌的这样一位英雄般的人物,一个大山、大树、大象一般伟大的人物,经过时代现实的冲击以及骑马摔伤和更严重的中风之后,已经危在旦夕。作者将上尉的形象塑造得越是完美,一代拓荒者即将逝去的挽歌越是令人悲痛。对此,作者有着清醒认识:
“定居在古老西部的是那些梦想家、心胸宽广的探险家,他们不计实利,豪放爽朗;他们互相谦让,讲究义气,善于进取却不善于守业,所以他们只会征服,不能长治。”
艾林格、艾维——势利者的一代
福瑞斯特上尉和年轻一代人构成了两个等级分明的社会阶层。出入“福瑞斯特之家”的皆是社会名流,有权有势,是做大生意的。房子周围又宽敞又漂亮。家里请有佣人,家具陈设十分讲究,储藏柜里存着大量名酒。再看看那些普通谋生者的家庭:红头发小孩儿的爸爸是卖肉的,两个双胞胎的爸爸是镇上一家杂货铺的老板,艾德的爸爸是开鞋店的,另外两个衣着破烂、头发乱蓬蓬的孩子,他们的父亲则是德国裁缝。他们大多清楚这样一件事实,“社会上明摆着有这幺一个幸运的特权阶级”,“有钱的幸福的人也是享有特权的人”。
但艾维·彼得斯可就不这样想,他蓄意向这个特权阶层发起挑战。刚出场时,他那恶毒的形象便跃然纸上。他走到福瑞斯特太太的园子里,用弹弓打落一只啄木鸟,然后竟然用小刀狠狠地剜去了鸟儿的两个眼珠,残忍地看着它左冲右撞。在福瑞斯特太太家里,其他伙伴只敢待在走廊或者厨房,只有艾维留在后客厅,“双手叉在胸前,两眼眨也不眨,大胆地打量着周围的摆设”。
几年后,艾维·彼得斯当上了律师,通过各种不正当手段欺诈印第安人,做投机生意,侵吞田地。他一直觊觎上尉的家产和福瑞斯特太太的美貌。上尉家道中落时,他趁火打劫,租了他们家的那片草地,将沼泽地里的水吸干,改成麦田。要知道,这片沼泽地是上尉特意留出来,让它们空闲着,任青草发出银色的光泽;而艾维消灭了这片沼泽地,其实是消灭了一大片他所厌恶的东西,是向福瑞斯特表示挑战。此外,他还经常借着公事之名,大摇大摆地出入福瑞斯特家门,极其粗鲁无礼。
而另一位福瑞斯特太太曾经中意的男人——弗兰克·艾林格,也是一个伪君子,一个厚颜无耻的势利之徒。他常穿着一件印有青蛙图案的毛皮里子大衣,像一只充满欲望的野兽。在上尉家聚餐,他贪杯白兰地,喝醉了又和女主人眉来眼去。其后果然骗取了福瑞福特太太的美色,等到这一家人垮掉时,他又迅速娶了年轻貌美的康斯坦丝小姐。闻得消息,福瑞斯特太太绝望大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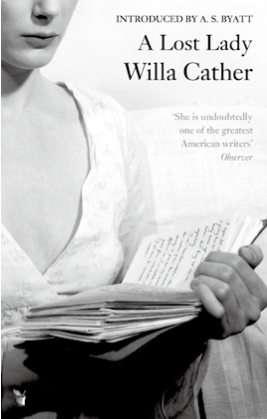
作者通过另一位人物尼尔的视角,愤慨地痛斥了年轻一代的势利:
“现在,他们(指福瑞斯特为代表的拓荒者一代)所获取的大片土地落到了像艾维·彼得斯这样的人手里,这种人从来不敢大胆干什幺事,从来不冒风险。他们享尽别人的幻景,驱散早晨的新鲜空气,挖掉伟大的自由的思索精神,铲除伟大的占有土地的人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这一大片空旷的土地,这些色彩,拓荒者这种无拘无束的王子派头,都被他们摧毁了,割裂成一块块有利可图的小片,好比火柴厂把原始森林切割成一根根火柴。”
时代的变化是无情的。上尉不久病逝。福瑞斯特太太和艾维形影不离。再不久,尼尔离开甜水镇,听闻艾维已经占有了上尉家的房子,另娶新欢,而福瑞斯特太太流落他方。挽歌声起,一个伟大的时代终究是逝去了。
作者痛斥年轻一代毁掉了拓荒者的一切,占有了他们的土地,瓦解掉他们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可是把时间追溯到几十年前,这不也同样适用于上尉一代对印第安土着的摧毁吗?三代人仿佛走了一个轮回,或者更准确地说,一代人取代上一代人拼的不过是武力、势力、机诈和野蛮的征服罢了,只是手段的好坏优劣不同,实质性的东西并没有变。
然而,谁才是这片土地上真正的主人?在另一部小说《哦,拓荒者》中,女主人公最后感叹道:“土地是属于未来的……我们不过是匆匆的过客,而土地才是永恒的。只有真正热爱土地,珍惜土地的人才配拥有它——哪怕这样也是短暂的。”如此看来,艾维·彼得斯之流显然没有资格真正拥有土地。并且,以他们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崛起,彻底埋葬了薇拉·凯瑟眼中辉煌的拓荒者一代,“拓荒精神”更是荡然无存。因此,挽歌是为这个物质化时代奏响的,当然包括“毒艾维”和唯利是图者艾林格之流。
美国批评家麦克斯威尔·盖斯马尔认为薇拉·凯瑟是“荒野中的一位贵妇人”,是“工业社会中一位重农作家”,她所捍卫的是不断物质化文明中的精神美。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很多过去美好的事物被破坏,尤其是“一战”后,薇拉·凯瑟逐渐对现实感到失望和迷茫,因而更加缅怀过去的辉煌,但逝去的早已逝去。这曲挽歌通过小说为时代奏响,也是从作家心底所流淌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