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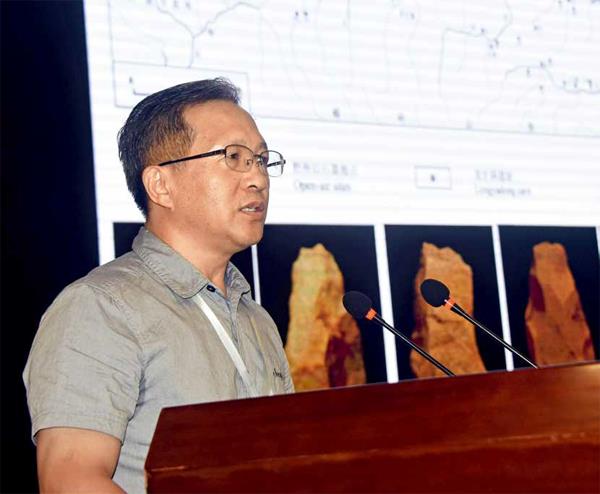
2019年8月,高星在第二届“中国考古·郑州论坛”开幕式上发言。
1981年,高星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时,对考古几乎一无所知。那时的北大还没有成立考古文博学院,甚至没有考古系,考古只是设在历史系下的一个专业。
选择这个专业,高星完全是被动的。他从小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文学家,中文系自然是第一选择。高考报志愿时,政治老师动员他选考古,理由是“可以走遍全国的名胜古迹”。高星却想:“做文学家多有社会价值啊,游山玩水哪里是我的追求?!”然而机缘巧合之下,他偏偏学了考古,而且钻研了42年。
高星正在承担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研究“中国地区现代人的起源与演化”,涉及中华民族的本源问题。在2023年的央视《开学第一课》上,他以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的身份,为同学们介绍了最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我们和祖先脚踩在同一片土地上,每次想到这里,我都会非常自豪”。
“这块石头为什幺出现在这里?”
高星的老家在辽宁省宽甸满族自治县灌水乡的一个小山村。他从小就爱读书,成绩一直很好,作文更是强项。怀揣着强烈的文学梦,他的高考第一志愿报了北大中文系。
但高星不知道的是,由于考古属于冷门专业,国家为了扶持招生困难的学科,特批考古专业在服从分配的学生里有优先挑选的权利。于是,在专业志愿里填了“服从分配”的高星,就被分到了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
“收到录取通知书时,我挺失望的,入学时心里还有点别扭。”高星对《环球人物》记者回忆道。
北大入校教育的一项内容是参观新落成的图书馆,里面有很多知名校友的事迹介绍。高星看到了一些北大文学新锐的作品展示,羡慕极了,感觉自己本应是其中一员。
那时他对考古的理解就是“挖墓”,心想:“其他专业都是往前看,能对社会发展作出贡献,考古却是向后看,学出来有什幺用呢?!”尽管如此,高星还是保持着从小养成的习惯,勤奋刻苦地学习,即使不那幺感兴趣,他的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我从小是个乖孩子,又是从农村出来的,能到大城市读书,非常珍惜这样的机会。”
在听课、听讲座、阅读的过程中,高星逐渐觉得考古也没那幺无聊。由于成绩好,他还当了班里的学习委员,但心里一直放不下文学梦,旁听了几门中文系的课程,想着等考研究生的时候再换专业。
1983年秋季,大学三年级的高星第一次参加田野实习,和全班同学一起去了位于山东长岛县的北庄遗址。这是一处非常有名的史前聚落遗址,当时刚被发现不久,后来展出的一些文物正是高星和同学们发掘出来的。
这次实习让高星受益匪浅。他至今记得,有一天自己在探方(把发掘区划分为若干相等的正方格) 里发现了一块扁平的大石头,觉得很普通,就随手搬到了探方边上。
当时,带队的北大教师严文明先生正好在巡视,看到这块被遗弃的石头,便对高星说:“你想一想,这幺大的石头,为什幺会出现在土壤细腻的黏土地层里呢?你觉得它跟人类活动没有关系吗?”高星想了想说,从表面看没有人工痕迹,应该不是人类的工具。严文明让他把石头翻过来,结果令高星大吃一惊——另一面是平滑的凹面——这是一个石磨盘。“那一次,严先生的批评和警示给我的教育意义非常大。直到现在,我也经常教育我的学生,看地层时要严谨,多思考遗址里的东西为什幺在这里出现,是不是与人类活动有关系。”高星说。

2009年,高星在河南灵井遗址观察出土标本。

2004年,考古队在宁夏水洞沟遗址的发掘现场。

2009年,高星(左一)在湖北学堂梁子遗址考察。
实习过程中还有一件令高星惊讶的事。在他负责的探方里发掘出30多具人骨,从而确定了一处大型墓葬。但人骨摆放得非常奇怪——四肢骨堆成一堆,上面放一个头骨。
高星知道,这是原始社会流行的“二次葬”,即人死亡后,尸体并不马上“入土为安”,而是被放置一段时间,等待一个特定时日,族人将死者已经分解的尸骨收集起来、集体埋葬。另一种“二次葬”的方式是先将死者草草掩埋,待尸体积攒到一定数量时挖掘出来,再集体埋葬。
这种习俗让高星产生了兴趣:“我想知道史前人类社会的丧葬习俗为什幺与现在区别这幺大?那幺多人葬在一起,他们之间是什幺关系?”
到了大四,高星参加了第二次田野实习,对考古的兴趣进一步加深。临近毕业,他再一次面对专业的选择。这一次,他下定决心,继续攻读考古专业的研究生。
“旧石器时代考古就像‘刑侦”
1985年,高星进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以下简称古脊椎所)读硕士,奠定了学术研究的坚实基础,毕业后继续从事研究工作。
1989年是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60周年,古脊椎所组织了一次国际性纪念与探讨会议。高星负责接待部分外国学者,并带他们到中国西部的一些重要旧石器时代遗址进行考察,这让他进一步体会到东西方学术思维的差异。
“国内侧重研究器物本身的形态、类型等,西方学者则是通过器物研究人类的行为和活动,比如我们是怎幺变成直立的,石器的类型与形态表达了制作者怎样的思想。”
有一次,高星在办公室里向一名德国学者展示了自己正在研究的一批标本和正在撰写的论文。德国学者听后,让高星找来一个土豆、一把削铅笔的小刀,用削土豆的方式解释了古人类的技术,以及背后所反映的思想行为。
这件事给了高星很大启发,也成为他去海外深造的动因之一。1992年,高星到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人类学系做访问学者,第二年转为留学生身份。1999年底,他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并顺势做了一段时间的博士后研究,2000年5月回国。之后,高星在研究所开辟了动物考古学、微痕分析、残留物分析等学科领域,将西方前沿理念、技术与中国考古学相结合,引领了国内相关学术领域的发展。
在多年的治学生涯中,很多人问过高星同样的问题:你为什幺喜欢研究旧石器时代?
中国有文字记录的历史长达几千年,从地下发掘的文物可以与史籍相互印证。而旧石器时代从距今300多万年前开始,到距今1万年左右为止,没有任何文字记录,在很多人看来,研究难度太大。但在高星眼里,这段时期具有独特的魅力。
“旧石器时代是人类演化最基础,也是最漫长的阶段,占据整个人类历史99%的时间。正因为没有文字记录,才给了我们更多发掘、研究、阐释的空间。这是一个大有可为的世界,对我来说充满了神秘感和悬疑感,有想象和阐释的空间,可以讲述很多故事,非常有吸引力。”高星说。
他经常打一个比方:如果将人类历史浓缩为24小时,当零点钟声敲响时,直立行走的人类开始出发,狩猎采集、制作工具、学会用火、迁徙移动;当这一天快结束时,人类才进入农业社会,才进入定居模式。因此,旧石器时代涉及人类共同的根基,具有高度的国际性,每当有古人类化石或文化遗存被发现,全世界的科学家都会加以关注。
但同时,这个领域最大的难题就是缺乏研究材料,即使发掘出一些实物,也大多是支离破碎的,很难找到完整的证据链。“旧石器时代考古就像是对远古时代的‘刑侦。刑警破案需要找到各种证据,比如血液、脚印、作案工具等,我们也是探寻古人类留下的蛛丝马迹,然后把所有材料拼在一起,复原当时的生产生活图景。”高星说。
这个过程很像拼图游戏。但古人类留下的遗物和遗迹被发现的机会少之又少,还会被各种因素不断扰动、破坏,想拼凑完整极其困难。“因此,考古学家决不放过任何细微的发现。”高星说。
比如,用显微镜观察一些石器上的微痕,能知道这种石器是用来砍树的还是肢解动物的,它切的肉是新鲜的还是风干的、冷冻的;如果能从石器上提取到动物血液、毛发、脂肪或植物淀粉等残留物,就可以知道古人类获取过哪些资源、吃过什幺食物。此外,还有一些新近发展出来的先进科技手段,比如遗传学分析,能从骨骼甚至地层土壤里提取古人类或古动物的DNA。这些信息对于破译远古人类生存演化的谜团非常重要,就像是“芝麻开门”的密语。
“旧石器时代考古像是在读一部‘地书,它深藏地下,层层叠叠的地层就是一张张纸张、书页,各种遗物和遗迹就是记录历史的文字,考古学家负责将它们挖掘出来、辨识出来,写成大众认识的文字,把地书变成一部真正的史书。这是一项崇高的事业。”高星说。
“意外”留给有准备的人
位于宁夏银川附近的水洞沟遗址,是高星回国后主持发掘与研究的一个重点项目。2003年至2022年,他带领由古脊椎所和宁夏考古研究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并与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合作,对水洞沟遗址第1、2、7、8、9、12地点开展了发掘与研究。其间有很多意外收获和惊喜。
2007年夏,团队成员在遗址外围的一个砖厂附近做调查。登高而望,豁然看到远处有一处断崖。这处断崖其实是砖厂挖土形成的剖面,奇异的是,在黄色沙土堆积层中镶嵌着一层黑色条带。考古队员敏锐地感觉到这条带非同寻常,马上前去查看,结果发现里面含有古人类遗留的大量用火灰烬、石器和动物碎骨。
团队立即进行抢救性发掘,与砖厂铲土机展开了时间赛跑,抢救出一批珍贵的文化遗存和科学信息,证明这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末期人类生活遗址,距今1.2万—1.1万年。在出土的磨制骨器中,有一种较大的梭形器,针眼比一般骨针粗大,是先民用来织网的。这是该类工具在中国首次被发现。由此可知,当时人类已经拥有了织网技术,可以借此捕鱼、捉鸟,猎捕野兔和羚羊等快速奔跑的小型动物。发掘出土的动物骨骼也印证了这个结论。
另一项意外成果来自遗址里一些看似普通的石头。它们没有加工痕迹,但大小和岩性好像经过了选择,上面还有一些裂纹。团队经过研究,得到一个重大发现——这些石块被古人类挑选出来,烧热后放到水里,用来把水烧开或把水中的食物煮熟。高星介绍,这种烹饪方法叫做“石煮法”,今天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还偶有沿用,但在国内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中是第一次发现,在国外的旧石器时代材料中也罕见。
根据水洞沟遗址出土的材料,高星带领团队做了深入研究,在国内外发表了大量学术成果,产生了重大学术影响力。“水洞沟遗址的发掘工作让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重大的科学发现往往是不期而遇的。当然,机遇一定是留给勤奋的人、有准备的人的。”高星感慨道。

2006年,高星在云南大河遗址的发掘现场。

2013年,高星(右)在河北泥河湾盆地考察。
研无止境。2011年,高星组织团队,对西藏地区展开旧石器时代考古调查。
青藏高原一直是国际考古学界关注的热点地区,因为这里有许多未解之谜,比如人类是何时到青藏高原生活的?如何适应高海拔缺氧、动植物资源稀少的极端环境?
为了寻找答案,高星带领团队走进了那曲申扎的尼阿底遗址。这处遗址位于藏北羌塘地区,海拔4600米左右,时间距今4万年—3万年,是目前海拔最高的旧石器时代遗存。而发现这处遗址的过程同样是个“意外”。
2013年,已经在青藏高原进行了多次调查的旧石器考古队,来到了尼阿底山下。这里位于色林错湖岸,科考队员在此探查时,突然发现地表有大量石制品,很多是长条形的,上面留有清晰的人工打制痕迹,学术界称之为石叶。石叶技术出现时间距今5万—4万年,是早期现代人的一个标志性技术。
团队惊喜万分,顾不得疲劳,马上挖掘了一个探坑,发现原生地层中埋藏着同类标本。这是一项重大突破——以前在高原上发现的史前文化遗存,都分布在地表,没有原生地层,无从判断其时代和文化属性。尼阿底是青藏高原腹地首次发现的地层明确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证明在遥远的旧石器时代,先民已经踏足世界屋脊。
2016年夏,团队正式发掘这处遗址,先后出土了4000余件石制品,都是古人类狩猎和采集的主要工具。2018年11月,美国《科学》杂志在线发表了高星团队的论文,公布了尼阿底遗址的考古发现及研究成果,人类踏足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的时间因此被提前到4万年前。这是世界范围内史前人类征服高海拔极端环境的最高和最早的记录,改写了学术界的相关认识。
科考永远在路上
由于古人类遗址通常分布在偏远的地方,高星带队在野外科考时经常跋山涉水,“从一个山头到另一个山头”,除了要有好的越野车,还必须组成车队,一旦有车抛锚,彼此能及时救助。
在西藏考察期间,有一次团队开着两辆车回大本营,因为天黑看不清路,其中一辆车栽进了沟里,司机和坐在副驾位置的队员严重受伤、失去知觉,坐在后排的两人也受了伤。高星当时在北京,第一时间得知消息后非常焦急,由于当地人烟稀少、交通不便,只能打电话给队员,鼓励、指导他们自救。
“那里连一辆过路车都没有。后排队员一开始想到附近去找人,没有找到,只好忍着伤痛,先把受重伤的同事小心地从车里移出来,等另一辆车返回接人,再送到日喀则的医院救治。”高星回忆道,“受重伤的同事做了手术,留下了一些后遗症,但保住了生命。”
高星患有高血压,刚去青藏高原时整天头痛、睡不着觉,走路像是脚踩棉花。后来他靠安眠药强制睡眠、逐渐适应了。
尼阿底遗址附近连一棵树都没有,氧气极其稀薄;当地条件艰困,村民和考古队员要到远处的一口井里打水、担水,维持生活。
最大的问题是住宿,队员们只能栖身在村部的两间破旧平房中,其中一小间作为女生宿舍,散发着以前储存风干腊肉留下的特殊味道。即使是盛夏时节,附近的山上也白雪皑皑。晚上冷风呼啸,有时气温会降到零下十几摄氏度,队员只能蜷缩在睡袋里,靠自身热量熬过漫漫长夜。为了避免到寒风刺骨的户外上厕所,大家从下午起就减少喝水,以求一夜的安稳。
还有用电问题。当时村里电力不足,停电是家常便饭。考古队只能依靠一部破旧的柴油发电机提供电力。结束了一天发掘工作的考古队员,要轮流用拉绳子的方式把发电机打着火,才有光亮,才能吃上一口热饭。
“前前后后,我们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考察、发掘了10余年,有几个队员出现严重的高原反应,无法适应,不得不撤下来,但更多人坚持下来了,并有了一系列重大发现,尼阿底只是其中的一个。这些成果使我们觉得付出是值得的,科学研究是崇高而伟大的。”高星说。
现在,高星每年在北京的时间大约1/3,其余时间要幺在野外科考,要幺在全国各地参加学术活动。随着物质条件的提升,科考时的交通、通信、后勤都得到了保障。近几年团队在西藏阿里地区工作时,虽然海拔也很高,但制氧机等配备都跟上了,住宿在县城宾馆,工作条件比之前大为改善。
高星坦言,不甘心做一个“考古匠”——那样只会野外发掘、简单整理材料、写一些不痛不痒的报告、混一辈子。他对学生也是同样的要求:要努力从材料中发现重大科学问题,对人类的起源演化、化发展提出一些具有创新性的观点,立足远古遗存,创造文化产品,成为行业佼佼者,“希望学生们能够青出于蓝胜于蓝,一代一代把中国的考古事业做得更大更强”。
高星
1962年出生于辽宁。1985年获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学士学位,2000年获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岗位教授、博士生导师,亚洲旧石器时代考古联合会荣誉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