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三洲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沈从文(1902-1988)是极具传奇色彩的一位大家。作为一个土家族作家,他只接受过小学教育,甚至连标点符号也不会用,却以一个下层士兵的身份起步,成为使全世界为之瞩目的著名作家,并且到西南联大教写作、在北京大学当教授。
上世纪20年代初期,当沈从文沦落困顿在北京城并试着以投稿糊口时,曾被当时著名的“副刊大王”孙伏园开玩笑,把他的几十篇作品连成一长段,当众摊开后说,这是某某大作家的作品!说完后扭成一团,丢进了字纸篓。其实,沈从文也承认自己“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过他当年报考燕京大学时,“一问三不知,得个零分,连两元钱报名费也退还,三年后,燕大却想聘我当教师,我倒不便答应了”。第一个发现沈从文文学才气的是郁达夫,把他引进文学殿堂的则是徐志摩。郁达夫那篇著名的《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就是在1923年收到沈从文的求助信后给他的回信。后来,沈从文终于在文坛上登堂入室了,他的一部中篇《边城》,足以让他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留名,他的《湘西》、《长河》和《湘行散记》,至今依然脍炙人口、畅销不衰。
一
“乡下人”不仅对文学有一股子执着劲儿,对爱情也同样如此。1928年8月,沈从文应胡适之邀,以小学毕业的资历担任上海“中国公学”的讲师,讲授写作。在这里,沈从文遇上了让他一见钟情的张兆和,从此开始了漫长的以写信为方式的求爱历程。沈从文跟得很紧,追得很累,而张兆和只是沉默,并对男方那连篇累牍的情书不胜其烦,曾找到校长胡适说:“我顽固地不爱他。”可沈从文不管这些,依旧殷勤地写着他的情书,依旧娓娓道来爱她的理由,从平淡的文字中,透露出一种“舍你其谁”的至诚韧劲儿。1933年5月,丁玲被捕后失踪,引起文坛瞩目。两个月后,当人们快要忘记丁玲时,沈从文发表了《记丁玲女士》一文,不仅引发了两个多年旧友之间的是非恩怨,也成了一桩难了的文坛公案。同年9月,苦苦追求的爱情终于有了结果,沈从文与张兆和终成眷属。

《沈从文传》,(美)金介甫著,符家钦译,国际文化出版社2009年3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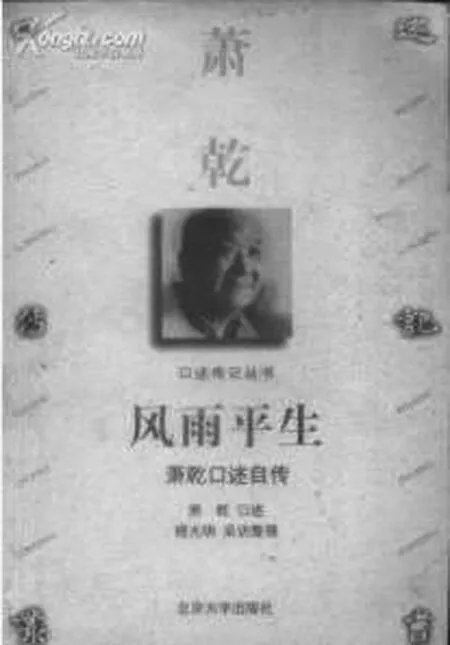
《风雨平生:萧干口述自传》,萧干口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3月版。
沈从文的文章,曾多次在文坛上引起论争,著名的“京派”与“海派”之争,就是因为他的文章而引发的。可新中国以后,沈从文这个名字,几乎从文字版的现代文学史上消失了,现在我们能读到与他有关的新文学史料,几乎都是在新时期拨乱反正后披露的。
印象中的沈先生,一如他笔下的湘西风景那样,宁静淡泊,遗世独立,有时候甚至还有些胆小怕事、处处与世无争的样子。比如,他写了近30年的小说散文,到了1947年10月,在他写完了自己的最后一篇小说《传奇不奇》后,一看形势对自己不利,就此封笔了。解放以后,作为“地主阶级的弄臣”、“清客文丐”、“反动文人”和“带着桃红色”的沈从文,尽管著作等身,但一看到第一届文代会上没有他的名字,立刻从迷惘徘徊中惊醒,陷入更可怕的孤独落寞之中。他惶惶不可终日,原指望能让从解放区来的、现已当上文艺界高官的老朋友丁玲帮上他一把,没想到事与愿违,丁玲对昔日的旧友根本就不屑一顾。那时候,全社会都在向往革命,追求进步。妻子张兆和去了华北大学学习马克思主义;以前曾经热烈追求过她的历史学家吴晗,当上了北京市副市长,身份要比自己显赫得多;连自己的儿子,也要跟他讲政治大道理了。整个社会以及家庭的革命氛围,给沈从文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于是,这位“五四”时期的名作家经常是深夜埋头写作,第二天早上却又把写好的东西毁掉。在孤立无援、惊恐不安中,他竟然选择了自杀这条绝路。方式是喝了煤油又割了手腕,幸而昏迷几天后幸而被救活,但留下的心灵伤害,却是永久的。从此,他辞别文坛,大隐于市,远离政治而改为研究历史,到历史博物馆去默默潜心古代服饰研究了。1963年,他受周恩来的委托,负责编写《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以不到两年的时间完成了这部书的初稿。周恩来看了之后,说:“出版后就可以作为国礼送给外宾了。”可惜随后“文革”爆发,出版计划搁置,一直到1981年才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
沈从文有一句名言,即“人生是一本大书”。他的一生,可谓是谨小慎微、兢兢业业、冷静旁观的一本大书,如季羡林悼文中所称,是“一生安贫乐道,淡泊宁静”。据美籍沈从文研究专家金介甫的《沈从文传》说,到了50年代中晚期,沈先生逐渐适应了社会进步,他的确感到“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清除了内战、帝国主义、饥饿和鸦片。作为政协委员,他一方面在会上自我批评,告别旧我,承认自己属于旧知识分子,是屠格涅夫小说中“多余的人”;另一方面又于1956年重返湘西,并将他的返乡见闻写成《新湘行记》,颂扬新中国的建设成果,表明自己向党和人民靠拢的心迹。苏联的第一个宇宙飞船飞上太空时,沈从文亦为此激动不已,说“此时真想入党作为纪念”。不过,他的热情毕竟有限,当他的朋友丁西林和张奚若动员他申请加入共产党时,他却说“没兴趣”,始终与政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1961年,他还与18名青年作家一同登上革命圣地井冈山,尝试写一部以革命烈士为主角的长篇小说,结果三个月后无功而返。即便如此,沈从文在“文革”期间却依旧摆脱不了政治的困扰和人事的纷争。
据陈徒手《午门下的沈从文》一文所述,当时,写大字报揭发他最多的居然是自己曾经帮助过的画家范曾。他在大字报上说沈从文“头上长脓包,烂透了。写黄色小说,开黄色舞会”。对这种肆意构陷和无限上纲,沈从文在大字报上面写下了八个字来表达自己的愤怒:“十分痛苦,巨大震动。”他在回复的大字报上说,“过去老话说,十大罪状已够致人于死地,范曾一下子竟写出几百条,若果主要目的,是使我在群众中威风扫地,可以说是完全作到了……即使如此,我还是对范曾同志十分感谢,因为他教育了我,懂事一点,什么是‘损人利己’。可说是收获之一。”这件事也成为他晚年心境最感震惊和伤害最大的一件事,使他从此再也不提范曾这个名字。前些年,范曾就此事还曾做过一番自我辩解,后来也就不清不白地撂下不提了。
二
沈从文的一生,培育扶持过不少青年作家。然而,作为他当年的得意门生、作家萧干(1910-1999)在去世前曾出版过一本《风雨平生》的口述自传,首次透露出生性孱弱、宅心仁厚的沈从文,也曾用过“揭发”、“划清界限”这种类似的方式,对待过自己的“右派”学生萧干。
1999年1月30日,萧干在他的最后遗作里,又详细述说了这件事情:“人家都说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大弟子,其实我在文学道路上得到沈从文的指引提携,比汪曾祺要早。他是我的恩师之一,1930年把我引上文艺道路,我最初的几篇习作上,都有他修改过的笔迹。”萧干30年代的成名之作《篱下集》,就是沈从文潜心修改的。然而到了20年后的“反右”期间,在文联大楼一次公开的批判大会上,萧干想不到沈从文会站起来积极发言,并耸人听闻地揭发自己的学生说:“我知道萧干早在1930年就同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上了。”他指的是1929年萧干曾协助美国青年威廉·阿莱编过八期对外宣传中国新文学的英文刊物《中国简报》一事。对这件事,作为萧干的第一个文学老师的沈从文,应该是最了解情况的。这样的揭发出人意料,但作为学生的萧干,只是把这种现象看作是人在运动面前自保的一种方式,没有过多地去计较。因为在当时,只有像这样上纲上线,声嘶力竭地来批判对方,才能让大家相信他们之间已划清了界限。所以,那时候他们的师生关系还能够一直维持下去。
到了“文革”期间的残酷岁月,无路可走的萧干亦想走他老师沈从文曾走过的老路,以喝白酒服安眠药的方式自杀未遂。1972年,萧干从湖北干校回京治病,为解决自己的住房问题而四下奔波。在去看望沈从文时,见老师正在狭小的居室里编写《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于是便出于不忍之心,频频为沈从文呼吁扩大住房,还想托当时在北京市革委的一位朋友来帮忙。谁料沈从文得知此事后,不仅不领情,反为之动怒,二人在路上相遇后,便声色俱厉地痛骂萧干此举是影响了他的政治前途,怒斥道:“我的住房问题,用不着你张罗。你知不知道,我正在申请入党呢!”说罢,掉头不顾而去。为了此事,有着几十年师生之谊的两个友人,断然绝交,不复往来。后来,萧干还收到沈从文让夫人张兆和转来的一封亲笔信,说他一旦去世,不许萧干参加追悼会,亦不许他写悼念文章,不然的话就要诉诸法律。
萧干在一篇遗稿里写到,他并不认为老师真的要申请入党,他只不过在用这种方式表明,自己并没有像学生那样沦为次等公民,只是想在政治上占一个上风罢了。萧干的分析是对的,50年代末沈从文有条件入党,他尚不积极入党,更何况社会纷乱的“文革”期间呢。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随着政治环境的日益宽松,他们之间的关系也逐渐融合,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外界因素,师生二人始终未能再晤一面,以尽释前嫌。
现代著名作家夏衍,“文革”时身陷囹圄,孤愤之余,写下了言近旨远的《整人诗》:“闻道人须整,而今尽整人。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人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试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此诗原系清代前明遗老雪庵和尚做的《剃头歌》转化而来的:“闻道头须剃,而今尽剃头。有头皆可剃,不剃不成头。头自由他剃,头还是我头。试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几十年来,诚如上面两首打油诗所形容的,中国文坛上类似这种互相整治、冤冤相报的事例不胜枚举,有很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都表现出自己的两面性。如当年违心去批判胡风的巴金,到头来自己也成了文坛“黑老K”;几十年一贯正确的周扬,不但“文革”时遭受厄运,到晚年时也难逃被人批判而无处申辩的困境;“反右”期间引诱吴祖光出来“鸣放”结果把他打成右派的戏剧家田汉,自己在“文革”期间又遭到了灭顶之灾。仔细分析一下,这些现象只能用在政治高压下,知识分子所表现出的性格软弱、人性扭曲和性格分裂来解释。对此,我们可以从31卷本《沈从文全集》新增佚文中找到作者心灵轨迹转化的一些答案。
作者在“文革”期间上交的思想汇报《劳动感想》里,一方面忏悔自己“脱离人民过了六十多岁,过的完全是寄生虫的生活,不以为耻”;另一方面,又企盼着“但手中的笔还得用,将可用到讴歌这个地方人民的一切新成就”。看看这些沉痛的语言,不是告别旧我迎接新我的反思又是什么?所以,沈从文主动与自己的右派学生划清界限、说出自己正在申请入党的话语,都可视为是在非常时期里,人的生存本能的一种正常反应。
可以说,如果不是萧干本人出面来说这件事情的话,谁也不会想在沈从文身上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有评论家认为,在中国现当代文坛上,沈从文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因为他从不宣传自己,可他的作品却默默地从边城走向了世界,所以当年在提名他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时候,左中右都能接受。对此,2002年秋天,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马悦然在接受专访时证实:假如沈从文不是在1988年早些时候去世的话,该年10月公布的诺贝尔文学奖,极有可能会颁发给沈从文。马悦然表示,“对沈从文的钦佩和对他的回忆的深切尊敬”,促使他“打破了严守秘密的规矩”。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这不仅是沈从文的个人遗憾,也同样是中国文学的遗憾。然而,即便是没有这个奖项,即便有他学生萧干所讲的那些荒唐岁月中的伤怀往事,也无损于沈从文在世界文坛上有目共睹的文学成就。诚如著名的翻译家荒芜生前在写给沈从文一首诗中所吟唱的:“边城山色碧罗裙,小翠歌声处处闻;我论文学追五四,至今心仪沈从文。”
(选自《文笔》2012年3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