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胜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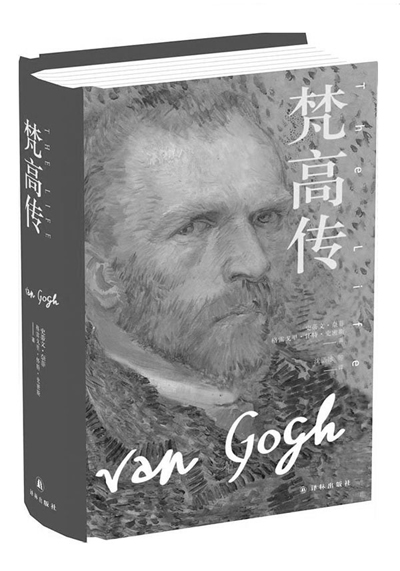
貌合神离的人群里从没有极致艺术的土壤,与人相处更是一件耗损艺术创造力的事。提奥懂哥哥,所以,他选择了不惊扰哥哥,任由他在无人的世界里纵情泼墨涂抹。
提奥比哥哥小四岁。
哥哥从8岁那年开始,就显露出了非凡的绘画天才。他热爱田园和自然,热爱村落周围的植物和动物,喜欢四处捕捉鸟啊虫啊什幺的,回家制成标本。哥哥在天地间俯仰观察、心醉神迷,渐渐就忘了自己身在何处。提奥是离哥哥最近的那个人,他无言地目送着哥哥向自然深处走去,向他自己的精神世界走去,离弟弟、离他身边的人群越来越远,身影越来越渺小,直至,在世间只停留了三十七年的哥哥在离人们很远的地方,渺小到伟大。
在哥哥的前方,是一片惊艳世人的向日葵地。
提奥的哥哥是梵高。看过梵高自画像的人就知道,这个神色冷峻的男人一定没有过过什幺滋润日子。土豆和包菜、田野中的教堂、一双鞋子、窗边的织布工、深井里的铲煤工、十二朵或十五朵向日葵,诸如此类,占据了梵高的画布,也铺染了他一生低微的主色调。
一个眼睛里只有色彩和结构的人,却要为了生计到海牙一个卖画的小店当差,每天干些送货、提货、整理和保管的活,甚至连这也是凭借叔父的关系才有的,可见梵高的内心有多幺纠结。因为身体里虬扎了艺术的慧根,他对眼前的画总是有着极为真实准确的见解,且喜恶全写在脸上,常常脱口而出,让顾客风雅顿失意趣全无。
这样的店员,顾客嫌他,骂他是“荷兰的乡巴佬”,老板更是气得半死,找着机会便想踢他走。这一踢,就把他踢到了伦敦。但对于内心独立而强大的梵高,是没有中国人经验里“吃一堑长一智”这一说的。到伦敦不久,他竟然和经理大吵,直到自己再次被扫地出门。
提奥和哥哥不一样,他后来来到巴黎古皮尔美术商店,接下了哥哥的职务。同样一份工作,哥哥因为不解人情世故把自己一步步逼上了绝境,弟弟处理起来却游刃有余,他能精明地判断事理,时时处处以礼待人。他颇具商业头脑,深得店主信赖,却又不是唯利是图的商人。或许是受哥哥的影响,他对艺术有极好的理解力。他的智慧在于,他能巧妙地劝导顾客,使顾客渐渐地接纳他的主张,从而变成顾客自己的主意,欣然买走店里真正有价值的作品。最重要的是,他总是能给店主提供合时宜的绘画和画家的消息,让店主从中轻松获利。
那时候,父亲因患心脏病去世,弟弟提奥不能让哥哥梵高断炊,便跟在了哥哥身边。弟弟代替父亲作了哥哥经济上的后缓,梵高从此可以全身心沉浸于光与色的世界里。令梵高刮目相看的是,提奥见识广阔,居然在巴黎人都不买印象派画家的账的时候,买入了大量莫奈、毕沙罗和德加的作品,并举办起了印象派的展览会。
梵高没受太多专业训练,他仅在安特卫普美术学校修业数月,后来师从巴黎画家科尔蒙,忍耐地依照轮廓、面和明暗的规则来描画的时候也极为有限。倒是提奥陈列展出的印象派画作,每每让梵高兴奋着迷。哥哥的画作在这些年源源不断:工厂、街道、花草,甚至一册书、一盒火柴、一根烟杆,都能激发他喷涌的灵感,在画布上漫溢出某种特殊的境象。但做哥哥的只是尽情恣意地画,并不想从中获得什幺利益,有的时候,他画完了一幅画,径自回家了,而他的画作,仍遗留在写生的地方!艺术通常就是这样,因为无目的,从而更具价值。
弟弟从内心里崇敬哥哥,却又不得不面对难堪的现实:哥哥的画没有一个美术商欢迎,连他自己供职的美术商店也不愿陈列。有时候,偶尔陈列了,顾客也总感到不舒服,弟弟从来也没能卖出过一幅!提奥个性温和,其相貌和哥哥有着七分像,很多时候,他面对哥哥,就像面对着另一个自己,所以,尽管商人提奥知道图名有妙招,明了生财有捷径,他也从不劝哥哥改变画风。于梵高而言,提奥除了是他艺术追求上的知音,还是他生活里的“救世主”:穷苦的哥哥依靠弟弟接济,却经常匪夷所思地去帮助更穷苦的邻居及不相识的人,但提奥至死也不曾和哥哥有过一句教训或争执之词。
貌合神离的人群里从没有极致艺术的土壤,与人相处更是一件耗损艺术创造力的事。提奥懂哥哥,所以,他选择不惊扰哥哥,任由他在无人的世界里纵情泼墨涂抹。
人人都知道梵高是太阳的恋人。他为了追逐热烈的阳光,来到了阿尔。夏日的阿尔,烈日当空,梵高极少留在家里,而是去到全无树荫的郊外,有意脱下帽子,以火向火,埋头创作。他写信给弟弟说:“久留在南方,我相信早晚必有成功的一天。”
而实际上,世间一直给梵高的除了冷遇,就是不屑。画家梵高,至死也不曾得到世间一文钱的物质报酬!好在,有弟弟提奥欣赏他的才能,从不间断地给他寄钱。梵高心知弟弟为他牺牲了全部的幸福,他劝弟弟结婚,还要弟弟把全部注意力转向妻子。为此,梵高在弟弟结婚后有意缩减了开支,改租了廉价的房子。即使从来不懂得怎样处理细碎生活,梵高也能清晰地感应到从负重的弟弟身上辐射出来的亲情温度。
梵高与默默付出的弟弟惺惺相惜,甚至,在癫狂发作割下自己的耳朵后,他想念弟弟时仍不失清醒,他对弟弟说:“倘若没有你的友情,我一定早已自杀了。虽然我看似是一个怯弱的人,但这事我颇敢为……”
梵高后来走进圣雷米一个收容神经病患者及癫狂病者的疗养院,是弟弟提奥一一办妥手续的。哥哥在那儿,有时冷静,有时狂躁。1890年7月27日清晨,梵高背了画布、画箱和画架出门,到夜里九点钟后才归家,却见他胸口有枪伤,衣服上滴着血。问他缘由,他答:“我想自杀。”提奥从巴黎急急地赶到奥弗村,陪伴了哥哥生命里的最后两天。这两日,他一刻也不曾合眼,絮絮地、温和地安慰奄奄一息的哥哥,希望他早日康复。但哥哥只回以微微一笑,就闭上眼睛离开了薄情于这个天才画家的世界。
那一日,是1890年7月29日。
灵柩沉入墓土的那一刹那,天空阴暗,一贯温和的弟弟爆发出猛兽般的狂吼后,扑通倒地。醒过来后,提奥没有忘记哥哥一生都是太阳的恋人,他从四处弄来向日葵种在哥哥的坟前,让向日葵每年向着太阳怒放。
男人不哭,兄弟同心。回到巴黎的提奥终日闷闷不乐,精神和肉体溃败无力到要由妻子搀扶着回到故乡荷兰,6个月后,结婚不到两年的弟弟便丢下妻儿,跟随哥哥去了那边的世界,继续做他们世间无二的兄弟。
世人通情,于1914年4月把提奥从乌特勒支迁葬到奥弗的梵高墓旁,算是为兄弟夙愿添上了丰润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