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建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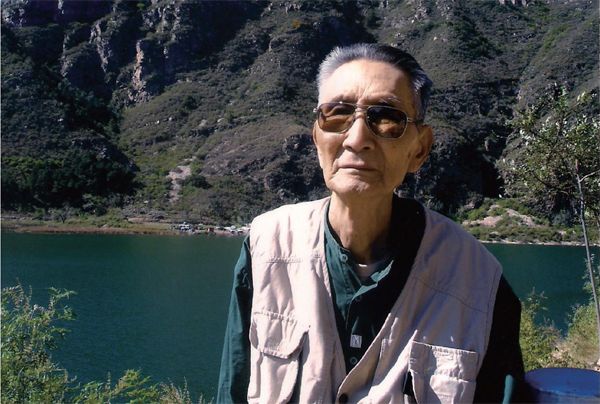


一
李纯一先生是我的研究生导师,但我从未叫过他“老师”。白打四十年前与他结识,我就一直称他为“李先生”。这个称呼从未改变,直到2019年我最后一次去北京老年医院看望他,李先生一如既往地叫我“小方”。在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他说:“小方,你的头发都白了。”2020年新冠肺炎肆虐,医院禁止亲属探望,这使2019年我与李先生的见面竟成为永别。
2021年1月15日,李先生仙逝,享年101岁。
李先生是1920年生人,但他常以虚岁算年龄,因此,我们这些学生们都认定他是102岁去世,与他的同事缪天瑞先生(1908—2009)寿年相同。
在音乐圈内,知晓李先生名字的人似乎并不太多。然而,在音乐学术界,尤其是中国音乐史学界,先生声名显赫,地位尊享。还由于他的研究涉及诸多学科领域,故在中国考古学、中国历史学乃至国外汉学界都颇有影响。学者刘再生先生称他为“乐史三公”之一,与杨荫浏、廖辅叔两位音乐史学家齐名。李先生的论着《先秦音乐史》和《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被学界称为“开创性着作”“开山之作”“拓荒之作”“先导范例”“标志性成果”等,前书还斩获第九届中国图书奖,可谓实至名归。至于他入选《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和德国的《MGG》音乐百科全书,获得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荣誉勋章等殊荣,业内人士亦都知晓。
二
李先生教过的学生少,因而他似乎从未有过一呼百应、众星捧月般的热闹和境遇。
他的学生中,蒋定穗是第一个,之后的秦序和我都是他的硕士研究生。秦序师兄毕业后留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工作,有机会常见到李先生。我毕业后赴西安音乐学院任教,虽然不能经常与先生见面,但长期保持通信联系。
我生性愚钝,虽然形式上毕了业,但自打1988年离开中国艺术研究院,李先生就不断指导着我的研究。诸多细节,我在《一位“没有毕业的学生”——我随李纯一先生学习音乐考古学》小文中业已述及。可以说,我就是李先生“面授”与“函授”教育的结果。
在一次交谈中,李先生告诉我,除我们三个嫡系学生外,他还有一些“私淑弟子”。如音乐史学家刘东升、西安琴家李明忠、西北大学教授赵丛苍、洛阳博物馆研究员高西省等都是他十分喜爱的学者。先生与他们亦师亦友,关系密切。
我曾经差一点就成为李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当年他为我攻读博士学位做了不少沟通协调工作,还设想过与他人共同担任我的博士导师。他甚至以宋新朝着《殷商文化区域研究》为例,让我思考博士论文选题,并提示我可以从事音乐考古分区研究。遗憾的是,彼时先生业已离休,加之当时各种规定和限制,此事虽几经努力但最终未能实现。
三
在李先生即将迈入95岁上寿之年时,秦序、李宏锋二位与我商议,意欲为先生举办一次贺寿和研讨活动。当时我正在湖北省博物馆考察,便将此情告知方勤馆长。方馆长对李先生十分景仰,他豪人快语,当即表示支持并慨允资助会议筹备和论文集出版事宜。于是,便有了2014年11月在厦门大学召开的中国博物馆协会乐器专委会年会暨第6届东亚音乐考古学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其中设立“李纯一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专题。李先生虽未能莅临会议,但通过录制视频向大会致辞并阐述了自己的音乐考古学理念。
紧接着是2014年12月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举办的“庆贺李纯一先生‘九五华诞学术研讨会”。活动当天,李先生坐着轮椅来到会场,主持人宣布请先生讲话,现场顿时肃静。他激动地说:“我平生第一次享受到如此宝贵的快乐和幸福!”闻听此言,我的脑海立刻回想起他多次向我述说的“文革”遭遇和不幸,禁不住热耳酸心,眼眶湿润。会后我去探望李先生,叮嘱他老人家:“您要健康地生活,我们期待庆祝您的百岁寿诞。”此言成真。2019年5月,音乐研究所如期举办“音乐考古学的新材料与新问题暨李纯一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为李先生百岁期颐颂寿。
这三次研讨会,全国有关学者云集。鲐背之年的90岁音乐史学家冯文慈先生发来贺词,耄耋学者陈应时先生也亲临祝贺。各路学者对李先生学术着作、学术思想和治学方略展开研讨。有关研究成果,见于随后陆续发表的论文和访谈等,并有专题文集辑录出版。
在依然健在的音乐学家当中,能够享有如此荣耀者实属不多。幸哉,李先生!
四
李先生的学术经历比较丰富,他常自嘲为“杂家”。
先生早年学习古典文献、训诂和考古,后来又学习作曲理论。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解放区开始教授音乐史,从此踏上治史之路,他戏称这是“历史的误会”。1957年,李先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一分册出版,后又于1964年出版该书的增订版。一般读者认为,既然是“分册”,作者大概要陆续推出其他分册,完成音乐通史的着述。然而,大约在60年代后期,李先生的研究开始转向,将自己的研究范围限定在先秦。
据我了解,李先生撰写音乐史的心路历程是有发展变化的。早期阶段,先生也想撰写古代音乐通史。他确实写过古代音乐通史类书稿。1953年《元明清时的音乐》撰就,次年完成《中国音乐简史稿》的写作。李先生将后书更名为《中国音乐简史》,并以油印本赠予杨荫浏先生,这部书稿现藏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
我指导的研究生余琛曾以李纯一先生早期音乐史着述为题撰写学位论文。她当年赴先生府上登门讨教,先生提供了这两部音乐史的手稿供其复印。《值得珍视的两部中国音乐史讲义手稿——记李纯一先生早期的中国音乐史研究》一文便是她研究成果的一部分。
后来,先生的治史理念发生了改变。新中国成立之后,音乐考古材料不断涌现。这时他意识到,古代音乐史研究仅依靠文献记载是不能反映真实历史面貌的,应该充分运用音乐考古材料。为此,他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到音乐考古研究之中。他先是完成《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一书,之后才开始撰作《先秦音乐史》。
他常对我讲,每个人的精力、时间、能力都是有限的,中国音乐史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个人要想全部研究精到是无法企及的。他认为,不少音乐通史类着述存在抄抄编编,陈陈相因的弊端。因此,他不主张大家都去搞通史,以为写通史的时机尚不成熟。他倡导多做一些专题性音乐史研究,在此基础上再编写通史。经过这样的学术思索,他毅然决定将自己的研究目标确定为先秦音乐断代史。
他告诫我,搞音乐史研究要当“作家”,不要当“编辑”,意思是研究要有所创新。大概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对于主编之类的头衔,凡有遨约者,先生都一概婉拒。
虽说李先生将自己的专业范围断在先秦,但他并非忽视整个中国古代音乐的历史脉络,也从未割裂先秦音乐与后世音乐的继承发展关系。实际上,他在汉代音乐史、中国乐律学史研究方面也颇有建树。1972年,他赴湖南长沙参与马王堆汉墓出土乐器的整理研究,并发表《汉瑟和楚瑟调弦的探索》一文,首次阐明汉代瑟以何种音阶结构来定弦。另外,他还撰有《中国古代杂技和音乐》,论述汉代以后杂技百戏的发展历史。李先生通览朱载堉着作,从中梳理分析,撰成名作《朱载堉十二平均律发明年代辨证》,将以往普遍认为的朱氏十二平均律发明年代(1584年)提前了3年,即1581年。别小看这3年,这是对中国律学史研究的重大贡献,它关系到朱载堉在世界音乐史和世界科技史上的显赫地位。
五
1996年面世的《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是20世纪中国音乐考古学的开拓性着作和标志性成果。该书除包括先秦音乐考古资料之外,也涵盖汉代音乐考古发现,先生将这一时间范围概括为“上古”。此书是先生的抗鼎之作,写作时间长达三十余年。1990年,他将书稿交付文物出版社,但由于种种原因拖延七年之久才得以付梓。李先生感叹,“着书固不容易,而出书也相当困难”。要不是他引据着作权法与出版社交涉,估计此书的出版还会推迟一段时间。
对于这部音乐考古学巨着,他已经做到“皓首穷经”了。他告诉我,新的音乐考古发现是层出不穷的,自己年事已高,恐不能再等了,否则到死也不能完成夙愿,因此他只好先行出版,容待日后再做增订。
李先生力戒仓促发表文字,他写完文章后都会先请师母阅读,且必须放置相当长的时间,期间还要不断修订,进行自我驳难,直到自己驳不倒自己才拿出来发表。如前述《朱载堉十二平均律发明年代辨证》一文,发表时已是“二十三年前写成的小稿”。
对于中国古代编钟的双音问题,他始终保留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尽管曾侯乙编钟明确标出了双音,但先秦编钟不一定普遍使用双音。编钟的合瓦形凹口钟体是其发出双音的关键,这是编钟自身的形制使然。如夏代的铜铃能够发出双音,商代的编庸(编铙)同样也能发出双音,但它们不一定被使用。西周之后的编钟也并非都应用双音。后来编钟的形制发生变化,它不是合瓦体而是正圆形,因此只能在鼓部正中发出单音。
李先生说,他的老友英国剑桥大学音乐史学家毕铿(Laurence Picken)也同意他的这种观点。从目前对先秦编钟的测音情况看,有些编钟确实是双音分离不明显,或是只能发单音。
2007年,我原本想请李先生来天津音乐学院讲学,但经过与先生家人商量,考虑到先生的健康和安全未敢邀他前来。取而代之的是,我委派天津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学生赴北京采访李先生。这次采访全程予以录音、录像,是一份十分珍贵的口述史料。在采访中,先生指出时下有些音乐考古研究仅做些图录画册之类,或是仅对乐器测音,这不是他心目中的音乐考古学。他还认为不能拔高古人,也不能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古代。
学生们将采访录音整理记录完毕后,交我审阅校核,之后又呈请先生过目。他删除了其中的一些段落,内容主要涉及对当时学术界不良风气和学术腐败现象的针砭和批评。我猜想先生可能觉得言辞过于尖锐,担心引起一些读者的不悦。此文后来以访谈问答形式在《天津音乐学院学报》上发表。
六
依我的认识,李先生的全部学术研究有一个发展的主线,即一手抓古代音乐文献,一手抓音乐考古资料。
在给我上课时,他多次强调《左传》是研究先秦音乐史的基础,必须要精读。同时,他还要求我学习版本、校勘、训诂知识,并尽可能了解古文字学和古音韵学的研究成果,他常说这些都是研究音乐史所必备的基本功。
李先生主张有多少材料说多少话,能一句话写完的绝不要写两句。他十分推崇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并举王氏的《观堂集林》为例向我讲述其中收录的文章是何等精炼。他说,你看王国维的文章篇幅不长,但字字千金,句句珠玑。李先生自己的文章同样是惜墨如金,朴实无华,深入浅出。他发表的文章如《说簧》《庸名探讨》《中原地区西周编钟的组合》《雨台山21号战国楚墓竹律复原探索》等皆其佳例,这些文章虽然仅两三千字,但均有创获,挤不出任何水份。
他讲究厚积薄发,这里仅举《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为例。在出土乐器总体分类上,该书将其分为击乐器、管乐器、弦乐器三类。在论述每种乐器时,开首即呈现一个型式划分表,以罗马数字标型,以阿拉伯数字分式,以英文小写字母划分亚式,之后是选择若干适例加以阐述和探讨。读者看到的乐器型式表是如此简明扼要,但岂不知背后要经过多长时间的材料梳理和反复研究。李先生积累了数不清的资料卡片和读书笔记,但用在他书中的材料是经过严格挑选的。他告诉我,考古发现的乐器有不少都是“大路货”。通过排比分析,选择具代表性的实例进行论述即可。当然,要优先选择科学的考古发掘品。
七
李先生的学术生命中,始终贯穿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他一生很少为人写书评或书序之类的文章。在可以数得来的几篇书评和序文中,他决非一味褒扬而是实事求是,既予以肯定,又指出存在的问题。
1996年,我将自己发表的论文结集出版,请先生作序。他不避师生之嫌,在书序中既对我的工作予以鼓励,同时又对我文章中存在的草率结论严厉批评,至今读来仍令我汗颜。
他常说,学术面前人人平等,无长幼尊卑之分。吕骥先生是他的老上级,但吕氏在论述新石器时代埙时,将不同地区出土埙的测音结果合并在一起,从而得出母系氏族社会后期已经产生五声音阶的结论。李先生撰文指出,这在研究方法上是不可取的。
李先生严于律己,更多的是自我批评。他在1974年写过一篇批判孔子“克己复礼”礼乐观的文章,刊于《考古学报》。我曾向他询及此文,先生十分自责,说这是他人生的“污点”。不难想见,在那个混乱无序的年代,又有谁能一点都不违心呢?
他曾在《先秦音乐史》中引用过“太室埙”,此项材料出自于省吾先生的着录。后来,我去山东省博物馆考察,发现该馆所藏“太室埙”为两面对开的“V”字形吹口,难以吹出声响,且陶埙铭文疑伪。我将此情告知先生后,他便在前述厦门会议中,以视频讲话的形式做出自我批评。
直到他百岁之时,仍然向我述说《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一书中对于某些乐器的类型学研究,由于乐器标本数量较少导致有些型式划分还存在问题。
八
李先生平时言语不多,但说起话来坚定有力。他为人耿直,说话从不拐弯。
他静修俭养,淡泊明志。他生活极为规律,没有不良嗜好。他说:“生活规律就是最好的养生之道。”年轻时他吸烟,戒烟后便收集各类烟盒,作为业余爱好。他患过胃病,手术后胃仅剩三分之一,故每餐食量很少。在饮食上,他的基本原则是“再好的东西我也不多吃,再不好的东西我也不少吃”。
我认识先生时就知他心脏不是太好。他体型瘦高,怕闷热,也惧寒冷。我秋冬季随先生外出考察时,每晚都想法给他加床被子。先生的起居时间固定,基本是雷打不动。他每天清晨三时左右起床,开始研究写作,或阅读和整理资料。中午一定要小憩一会儿,下午继续工作,并抽出时间外出散步或为家里购买生活用品。晚上必看《新闻联播》,七点半之后便上床睡觉。
先生的生活规律,在秦序师兄和我陪同他外出考察时依然严格保持不变。先生声称抗干扰能力极强,任何噪音都不能影响他的睡眠。
九
李先生心中总有“文革”的梦魇,一生挥之不去,直到生命的尽头。
他多次向我述说“文革”中的遭遇。1957年他被内定为“右派”份子,挨批斗、睡“牛棚”、下“干校”,与妻子、儿女三地分居。他曾经写好遗书几次准备自杀,但终因对亲人的不舍而未自尽。他视自己的名誉为生命。“文革”结束后,先生在8年之内共进行37次申诉,终于在28年后的1984年得以平反。
晚年时的李先生离群索居,自称过着半隐居生活。他离休后,举家搬至师母分配的总政干休所小区居住。他对我说,自己宁愿离新源里(音乐研究所旧址)远一点,免得触景生情,引发对“文革”的回忆。
在先生“九五”华诞研讨会上,他又禁不住重提自己的“文革”经历。女儿李青担心他情绪激动影响心脏,赶紧打断他的讲话。
这是李先生这代人的不幸!
虽历经痛苦和磨难,但李先生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在给我上课时,他常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加以阐释。他说,什幺是历史唯物主义?音乐史料就是物,这个物不能假,必须要真。真理是具体的,越具体就越深入。不能笼而统之,大而化之。他还以当年的“三讲”为例,以为“三讲”不能空谈,要具体讲,一具体就深入了。
或许有人会将《先秦音乐史》与他60年代出版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一分册相比,认为二者在唯物史观和阶级观念方面没有什幺变化,并颇不以为然。但我认为先生的音乐史着述实事求是,符合中国古代社会的实际,恐怕是不能轻易被否定的。
李先生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他认为做学问不能谬种流传,以讹传讹。他主张独立自主做学问,自己做学问要从难从严。“甘于寂寞,不为外物所动”,这是他经常教育我的口头禅。他对20世纪90年代知识份子“下海”经商颇有看法,总觉得那不是长久之计。他叮嘱我要安贫乐道,要甘做中国音乐考古事业的铺路石。
他早就手书“宁慢爬,勿稍歇”以及“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的座右铭予以自勉。85岁时,他完成《先秦音乐史》修订版;95岁时,他对《先秦音乐史》又一次补遗,并发表3篇有关编钟纹饰断代的研究论文。他的一生,践行着奋斗不息的“宁慢爬,勿稍歇”精神。
2019年4月6日,先生在北京老年医院手书与我:“为人光明正大,对党无限忠诚。要能包容忍耐,也要疾恶如仇,爱憎分明。”这是他为我上的最后一课。同年12月29日,《光明日报》记者刘平安去医院采访他,问他“有没有什幺遗憾”,先生答曰:“不能再为党做事了。”
音乐学家田青在李先生“九五”华诞时,曾题赠“寿”字芳墨,以为先生贺寿。百岁学人李纯一先生是伟大而高尚的仁者,他配得上“仁者寿”的荣耀和称号!
(责任编辑 荣英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