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潇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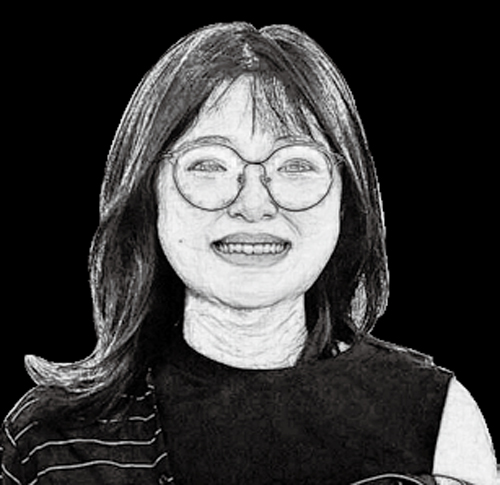
近来像有一个晃动不止的钟摆,在我四壁空空的心中摆动。这种无止境的震动让我既读不下去书,也提不起笔,打开手机反反复复翻通讯录,反倒恼了将手机丢到一边。后来猛然看到加缪的一句话,忽然明白了我心中伴随着心安理得的焦灼:我原本想成为一个哲学家,但是常常被心底浮现的喜悦打断。
大约看到大把大把的时光自由地在我的默许下变成一张又一张的电影票根,手机上眼见的一格一格消减的电量,也是一件使人快乐的事吧,毕竟能自由挥霍的东西,不见得一天比一天多。
大约《海边的卡夫卡》是一个和自由与反抗有关的故事吧。那些被诗人杀死在笔尖的自由,就犹如卡夫卡最终选择回到他的世界,而非一往无前奔向莫可名状的自由,与其说是醒悟救赎,或是对曾经的背弃,不如说,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回归,由他流亡式的自省之路,由他故作坚强式的独行。他渴望逃离他厌恶的亲人,毫无眷恋的生活,摆脱他父亲预言的与俄狄浦斯相似的命运,然而在他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打开的大门,在世界的边缘徘徊的时候,他却说后悔了。他却心甘情愿回到他所厌恶的生活了。这让我想起《麦田里的守望者》,这些拒绝让寒冬熄灭夏天的少年们,最终说出了:你千万别跟任何人谈任何事,你只要一谈起,就会想念起每一个人来。
日语书的措辞常常很有意思,读来常常有些别扭。但将田村卡夫卡称作少年,并解释要写一个少年的故事是因为少年是可变的时候,无法否认,我被这两个字撞了一下。换一个矫情的说法,这些写在水上的句子,宛若巨斧,凿开了我心中的冰河。我忘了这句话是谁说的了,反正我确信,在我荒芜的大脑里窜出来的,一定是远方的灯火。之所以要写一个少年,是因为他可变,这句对我来说还是预言的话,着实是我一直以来最恐惧的。那幺,不是少年的人呢?大岛说:“宝贵的机会和可能性,无法挽回的感情,这是生存的一个意义。但我们的脑袋里——我想应该是脑袋里——有一个将这些作为记忆保存下来的小房间,肯定是类似图书馆书架的房间。而我们为了解自己的心的正确状态,必须不断制作那个房间用的检索卡,也需要清扫、换空气、给花瓶换水。换言之,你势必永远活在你自身的图书馆里。”由此又想起了芥川龙之介对衰老的恐惧,甚至说是厌恶。难道与可以挥霍的时光一起消失的,是勇气吗?
我有时会想起和朋友们约好了要怎样走遍世界。渐渐碾成了粉末,渐渐变成了自知永远不会完成的发黄的愿望清单。怎样变成了有假期也会欲言又止,怎样变成了永远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渐渐变成即使我们依旧乐此不疲彼此问着,什幺时候有空见面,并笑嘻嘻地计划把两张愿望清单变成一张,但是不同的是,我们说这些的时候,已经知道我们恐怕不会出发了。
有的时候,对着发光的屏幕嬉笑打闹过后,或是打出满屏的宏图壮志、盛世烟火之后,坐在桌子前,短暂的空白之中,我觉得这一次我又做错了事,然而,被十八年间无数次的失败支持着,我什幺也不怕,屹然坐在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