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亭

进入第五年,“周围的世界”(The World Around)在样本广度上仍然是最能让观众突破舒适圈的建筑峰会。
今年它关注的是建筑与生态及社会正义的交叉点:从上海、越南、加纳到南美地区的建筑师逐一登台分享近作,展示出地域文化特征和气候差异带来的建筑类型的多样性。
可是当所有的实践派在庆祝时,意大利哲学家Emanuele Coccia泼了场哲学层面的冷水,对家的现代性提出了质疑:我们的居所,是一个过时的道德困局,也是阻碍我们真正拥抱现代性的障碍。建造住宅(家)的建筑师,不光是空间的艺术家,更是道德的工程师,如何理解这个新身份,需要所有建筑师在理论和实践中重新思考。
这些理论基于他2021年出版的《家的哲学》(Filosofia della Casa),其英文版《Philosophy of the Home》2024年4月刚刚由企鹅出版社出版。Emanuele Coccia出生于1976年,是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哲学家。他与其他哲学家不太相同的地方在于,常常与建筑师及设计师们有工作上的交叉:他曾协助Formafantasma设计工作室完成Cambio项目,也曾协助荷兰时尚摄影师Viviane Sassen,为其影集撰写时尚理论;还曾为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院长、景观建筑师Bas Smets的作品写书作序。
Coccia的一个中心论点是,无论从哲学还是建筑理论看,我们对居所的重视程度都不够。

建筑的教科书和典籍中,有关居所的建筑理论和实践总是被忽视的一部分。大部分的建筑理论着作如《向拉斯维加斯学习》《城市形象》《癫狂的纽约》等,都是关于城市的。在欧洲文化史上,城市也总是与哲学联系在一起,从雅典到罗马,从巴黎到耶路撒冷,城市是历史上技术创新、有偿劳动和大规模政治动乱的主要场所,也自然地受到柏拉图、霍布斯、卢梭和罗尔斯等哲学家和知识分子的关注,而家却被忽略了。
与之相对的,我们今天的居所形态并没有反映出人类住宅几个世纪以来的社会、道德和技术变革。“在巴黎,我们仍然住在19世纪的住宅里,这太疯狂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永远不会使用任何其他古老的东西,但我们接受古老的居所,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这种家庭生活形式固有的暴力。”Coccia此前在采访中提到,“它仍然让绝大多数建筑师坚持,每栋房子都是几个矩形的空间组合之一,每个矩形都被赋予了一些重要的用途”—卧室仍然仅仅是卧室,浴室也仍然是浴室。
这意味着,人们对重新定义住宅和房屋的必要性缺乏反思,人类的进步与家庭空间的想象力之间存在着差距,我们不得不从家庭内规模的角度重新思考共同生活的意义。家庭空间内的现代化仅与设备相关,那些提升我们生活品质的智能电气设备与空间本身并无关联。那我们的居所是什幺时候开始停止进化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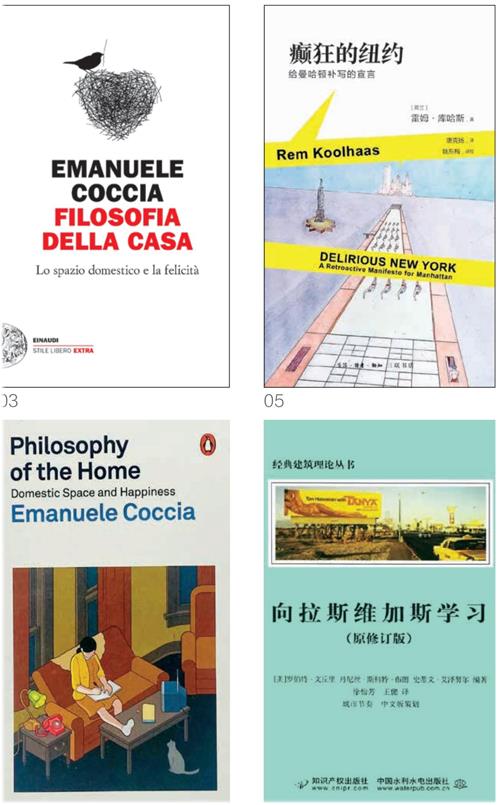
Coccia在“周围的世界”的讲座中引用了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对于现代性的定义:现代性不仅仅体现在技术发展、欧洲国家对地球其他部分的征服中,除了以政府形式为核心的社会秩序的转变,它还关乎一个革命性的道德计划。
这项道德工程将日常生活中最琐碎也最原始的特征—婚姻和工作—置于每一个政治、经济、社会和物质关注的中心。
我们之所以现代,不是因为生活在过度拥挤的城市里,手握着移动通讯设备,随时能通过高速列车和飞机远距离旅行,现代性是通过将工作这种创造财富的活动带出家的行为诞生的。而因为疫情产生的变化,让我们目睹了相反的过程:工作逐渐回归家庭,这也正在改变城市的结构。如果在家工作成为常态,就完全没有了为了生产和专业需求与其他人一起近距离工作的理由,结社的秩序就会变得任由心意。
1920年,柯布西耶写下了那句着名的建筑宣言“住宅是居住的机器”,展开了现代主义建筑的新篇章。据Coccia考证,柯布西耶是在1907年参观了佛罗伦萨附近的Certosa di ValdEma修道院的僧侣牢房后,首次想到了居住机器的概念。换言之,修道院的空间维度是现代建筑的基础。

当代住宅的构思、设计和建造仍然遵循两个世纪前的风俗习惯。“这个结果部分是由于国家和立法规定的惯性,部分由于建筑师的懒惰,部分源自于我们不想彻底改变我们的居所,因为我们想要的一切快乐都可以在城市中找到。”
《家的哲学》是Coccia在疫情期间撰写的,当时他深刻地感受到了被困于家里“如地狱般的痛苦”,以此为佐证,他在书里揭示了居所乃至城市关系的变化。
第一层道德困境,是如何将家的定义从空间结构中剥离出来。
移动手机和个人电脑,以及微信和WhatsApp这样的交流工具成了新的家庭空间。突破地域界限与住在远方的朋友和家人交流的行为,削弱了家作为功能结构的权威性。“智能手机本身或个人电脑是一个必须被视为家庭空间的物体。它确实是家的延伸。这意味着我们的家庭空间已经扩大,并且不再由空间和砖块组成。对我来说,What sApp是一种客厅,它将我的家变成了与空间或地理无关的东 西。”
无论我们去往何处,总有一个个连接朋友的房间跟随着我们。在“房间与地球重合”的现实下,居住在一个地球大小的房间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另一方面,地球入侵了所有的人类,入侵了我们的生活。

在家里,除了人类以外的所有活物成了我们的宠物。家是一个人将周围世界塑造成自己形象的产物,是为了构建我们自己并代表我们。真正的家成了我们逃离身份的地方,也是我们所爱之物逃离它们的身份的地方。
每个人都有过面对令人心烦焦躁的搬家纸箱的经历。作为一个曾搬家三十多次的高频移动者,多次搬运搬家纸箱和打包的体验让EmanueleCoccia意识到,体现我们生活的,并不是墙面和天花板,反而是我们在搬家时丢不掉的那些物品,比如衣服、书籍、器物和宠物。这些物品给予我们不可割舍的幸福感,而居所只是一个外壳。
“ 搬家,成了我们判断所钟爱的事物的奇怪又普遍的最后一个标准。”Coccia认为,无论是虚拟移动,还是越来越多人在物理层面的移动,在移动状态下理解家的内核将成为必要。
意大利设计师埃托·索特萨斯(Ettore Sottsass)曾在一本名为《空房子是谁的?》(Di c hi s ono l e c asevuote?)的精美小册子中谈到了“空荡荡的房子”,据索特萨斯观察,“穷人的房子通常都很小,空间局促,以至于里面的东西(桌子、椅子、柜子、箱子、大箱子、自行车、洋娃娃)永远不合适,它们堆积在每个角落,就像河湾处的漂浮物一样”。
矛盾的是,只有享有特权的人,才能通过清空家里的东西并假装贫穷来掩饰自己的特权。但这是表演性的展示,别无其他。卡戴珊的“赤贫风”是不是听上去就很熟悉?
第二个道德困局,是固有家庭单位被解构—即使是对社会住房最有远见的建造者,其作品的基本范式仍然基于父亲、母亲和孩子,但这个范式俨然正在受到挑战。
近十几年来,独居、丁克、性别革命、朋友群居,或是更为颠覆性的婚姻组合关系,都彰示着以爱为承载和主导的现代家庭关系,将打破固有的家族和血脉传承。这种新的组合方式逐渐在法国等地显现,而这种变化趋势应当得到法律和社会规则的承认。从人类学的角度看,它将永远地改变所谓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
在2021年书籍出版时,Coccia曾接受米兰国际家居展的采访,展望了新的家庭形式。“在很多方面,它都是关于爱的—关于关系和认同及其心理影响,关于以爱重新定义社会的力量。我意识到,要谈论爱,必须谈论新的家庭形式……我们通过婚姻制度达成的事情发生了巨变:家庭结构不再与遗产或家谱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改变的不仅仅是家庭,而是我们整个的经济结构。如果你不能通过遗产传承你所拥有的东西,那幺财产本身就不再有意义了。如果你死后必须归还所拥有的东西,那幺它就不是‘财产,而只是使用某些东西的权利。如果你的财产只是与你的生活方式相符的东西,那幺它就不是我们几个世纪以来所设想的不动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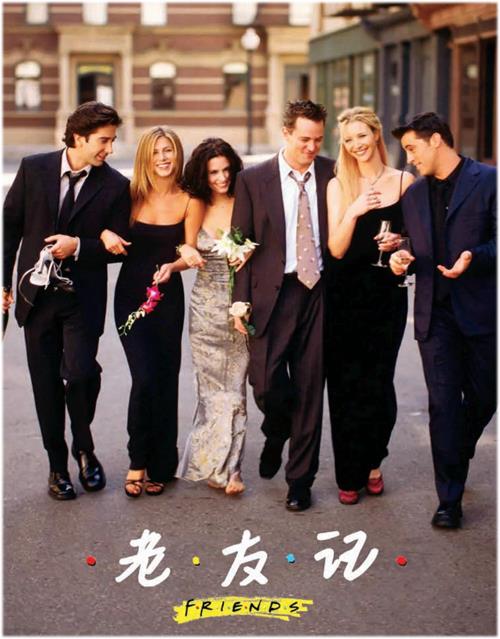
在演讲中他还引用了《老友记》,称它是一部令人难以置信的电视剧,因为它证明“家”可以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空间事实,“《老友记》很有趣,因为它描绘了一个不再与家谱联系在一起的家庭,那里没有孩子(当孩子出现,剧集也就面临了结束)”。
《老友记》中的这种理想状态被网友归纳成了“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人就在对面”,而在现实世界中,以山本理显的地域社会圈主义为代表的新型结构推动者,也证实了公众对最小社会单位存续的必要性的质疑。
也正是这些变化,迫切召唤着建筑形态上的重大变革。
“建设并不意味着摧毁一切。建造意味着你实际上必须面对过去。”Coccia说自己鼓励建造并且鼓励拆除,“人们总是声称出于历史和环境原因而保护旧东西,建筑文化也普遍接受了这种态度。你可以在最近几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上看到它。但你不能忽视我们在城市中的生活方式(的变化)。想想别墅的类型,这是一种自文艺复兴以来一直没有改变的保守形式。没有人尝试过想象我们如何在现有的居所空间内创新。”
在《家的哲学》之前,Coccia最出名的作品或许是2016年出版的《植物的生命》,那本书展现的是他对超越人类的物种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思考。他的作品经常质疑当代世界的物质性,其他作品涉及触觉、美学、城市空间和气候等主题。
在“周围的世界”这场分享会上的所有观点中,Coccia对于“爱”的依附会让人略表怀疑。或许他有其他尚未展开的细节和对爱的解读,总之单纯地想让人信服社会发展方向和结构整合将建立在爱的基础上,这与当下的现实有极大的差距。即使许多观点仍有争议,不可否认的是,Coccia的哲学观察引发了反思、思辨乃至争论。
《家的哲学》展现了现代社会中的困境:婚姻家庭作为基本社会单位的核心地位动摇,甚至像疫情这样的危机迫使人们对于曾经正常的空间形态感到排斥,对其背后陈旧的社会结构和遭到忽视的道德需求开始提出申诉。在演讲的最后,Coccia似乎把发展的信心投射到了欧洲国家以外,“没有一个欧洲国家的首都能够开发出适合本世纪的建筑语言。相对于西方以外的城市,我们生活在过去,却一直想象自己是当代世界的领导者。这是一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