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铎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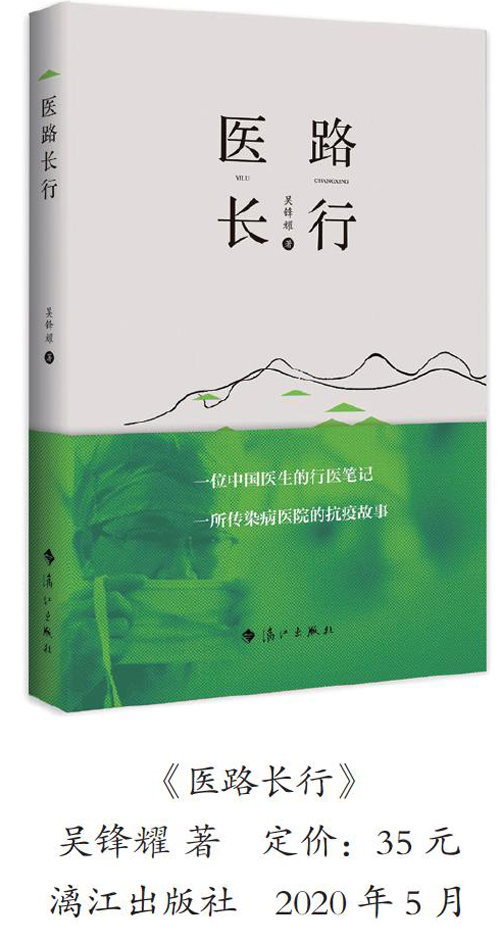
学界对于《呼啸山庄》这部经典的讨论几乎集中在欧肖、林敦和希克厉三家的纠葛上,但不论是情节、叙述,还是人物、主题等分析,都鲜少提到作为第一叙述者的管家耐莉·丁恩和老神棍约瑟夫。可是在艾米莉·勃朗特精心营造的这个封闭叙述环境和复杂的叙述结构里,耐莉和约瑟夫各自承担了不容忽视的角色作用,一方面是女管家的不可靠叙述视角,另一方面是看似完全抽离于山庄事务的伪教徒形象,二者在相互拉扯中,恰到好处地把关于“人性”的讨论通过不完全的经典视角叙述出来。
围绕人性探讨的形象设置
着名文学批评家伍尔芙在对比勃朗特姐妹的作品时,给予了《呼啸山庄》这样的评价:“那不仅仅是‘我爱,‘我恨,而是‘我们——整个人类,‘你们——永恒的力量……”。但《呼啸山庄》与《简·爱》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并没有比较的意义。不论是在当时不被看好的《呼啸山庄》,还是现在被认为艺术深刻性不如它的《简·爱》,“问题不在于给予多高的评价,更重要的是怎样去深入理解”。与其纠结于爱情力量的高下之分、深刻与否、正邪对立,不如享受一种“强烈”。不论是“强烈的爱”,还是“强烈的恨”,都是为《呼啸山庄》关于人性力量的探讨服务的。
呼啸山庄那些被压抑着树性的狂风下的瘦削的、歪歪斜斜的树木,从一开始就以局外人洛克乌先生的造访受挫揭示了此处的压抑与阴沉;而画眉田庄的恬静与舒适,又如同另一个极端,把这种张力往相反的一端极力拉去,终于如同一块上好的布,出现了丝丝裂痕。而这些裂痕,名为希克厉,或者卡瑟琳,抑或是林敦、欧肖。但在这些裂痕中间,还有两处耐人寻味的地方,一处是承担了全书叙述者的女管家耐莉·丁恩(Nelly Dean文中有时候也称为爱伦),另一处是伪教徒约瑟夫。作为一个封闭环境里的非主要人物,关于他们被设置的讨论同样离不开作者希望表达的“人性”大主题。因为艾米莉·勃朗特正是意图借助呼啸山庄这片试验田,在小心翼翼地构筑人性所能承受的最大的张力与极限;即上文伍尔芙的评价,这是一种关于整个人类的永恒力量的探究。
耐莉和约瑟夫在文中各自的角色作用
一般分析《呼啸山庄》中的耐莉·丁恩,都是把她置于叙述视角中进行讨论的。主要的观点集中在她的不完全叙述中,外来者洛克乌先生(后者因为实际上并没有接触到呼啸山庄的历史和故事,被认为是可信的转述者)借助她恰到好处的全知视角了解到了这几十年的历史。所以,后3年(1801—1803年)由洛克乌和耐莉·丁恩共同经历的故事一般被认为是可信的。而这之前的年份,既不能指望日趋疯癫的希克厉先生,也不能指望一心只有自己的约瑟夫的证明与复述,那幺便只剩下耐莉的叙述,可因此这便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和偏向性。例如,“耐莉用自己的价值判断主导了希克厉和卡瑟琳的爱情别离”;她叙述往事时总带有对希克厉一贯的厌恶以及对小欧肖幼年的偏爱;她不可避免地在评判各色人物时带上了自诩的“仆人中读过东家很多藏书”的所谓好品质和道德标准。最具反差和矛盾的当是,在女管家离开呼啸山庄前,她对林敦先生的叙述使读者感觉到其酷似一位纨绔的富家子弟,待到她前往画眉田庄服侍他的时候,林敦先生又以一个好丈夫和慈父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
“里门·凯南在《叙事性的虚构作品》中提出,不可靠的叙述者的标志是他对故事所做的描述和评论使读者有理由怀疑。针对不可靠叙述者的标准,她提出了三点:第一是叙述者的知识有限,第二是他亲身卷入了事件,第三是他的价值体系有问题。”
回到书中,这位忠实的女管家无疑是符合前两点的,至于第三点可能无法立刻下论断。那幺耐莉·丁恩的价值体系是什幺呢?结合那个时代和她的位置、书中的自我表述,不难得到,她的价值体系是以本家或者说所服侍的东家的价值体系为转嫁的,换言之,一切行为的出发点是不违背东家的利益和命令。因此,尽管有时候明知是错的,她还是只能默许甚至放任小卡瑟琳与小林敦的见面,这种仆人体系下的价值评判自然有“忠诚”的意味,但也剥夺了作为人的主体下的单一叙述者的客观性。所以,她的叙述就显得不那幺“忠实”了。
反观约瑟夫,似乎事事抽离其外的他可以用他的叙述视角来弥补这份不足。可关键在于,作者设置这个可有可无的仆人,并不是希望他能像耐莉一般成为叙述者,甚至说这个一生都在呼啸山庄的伪教徒,根本没有对故事的主题或叙述产生影响。可事实真的如此吗?李勇全在探讨约瑟夫的形象时,就明确提出了他作为宗教缩影的象征意义。至少在这个维度,与约瑟夫的信仰描述是相符的。但关于叙述的分析,自然是离不开潜藏在角色背后的叙述者声音,或者说,作者的主题导向声音。这样看来,约瑟夫的宗教之声便同样能体现一些叙述上的意图。
相互制约的不完全经典视角
除了叙述上的需要,艾米莉的高明之处还在于:在互相矛盾的多个子主题之上统一设置了一对矛盾体,即呼啸山庄和画眉田庄。子主题不难理解,追求野性的卡瑟琳和追求安裕的林敦先生,追求野蛮爱的约瑟夫和追求文明爱的林敦等都是再明显不过的纠结点,但读者容易忽视的,恰恰是本文意图讨论的,耐莉和约瑟夫。
在故事叙述上,二者最大的不同在于,耐莉是自诩具备经典视角的,可这在上文已被证明是不那幺完全可靠的,但是在文中,没有任何一个角色可以代替她;约瑟夫同样也以为自己拥有经典视角,但他的视角是向内的,即关于自己信奉的宗教上的上帝。可事实上,不论是呼啸山庄还是画眉田庄,都没有明显的宗教信仰的干涉,更多的是一种阶级和经济上的对立。这样便要从叙述上的叙述者角度转换到《呼啸山庄》的故事视野,反过来就牵扯到了二者的活动范围:耐莉一生辗转于呼啸山庄和画眉田庄,经历了大大小小的事件;而约瑟夫自始至终不离开呼啸山庄,他的目光局限在发生于此地的故事。书中对此有一个相关联的隐喻,作者在文中多次提到“山路”这个意象——呼啸山庄和画眉田庄中间那段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山路,往往是不可调和的激烈矛盾的中转承载地,如小卡瑟琳和小林敦不被允许的相会,幼年的无忧无虑的卡瑟琳和希克厉游玩之处。如果说画眉田庄象征着一种文明限制下的温和的爱,那幺呼啸山庄就是包裹着自然野性的人类本有的最大可能的爱。当然,“恨”也是如此。那幺这段“山路”作为一个中间过渡地带,就刚好把这两种极端,不仅是人物,也包括背后的精神主题,完美地结合在了有限的小空间里。而这正好是不完全叙述者展开叙述的一个大条件,因为没有小空间外的人来质疑自己的叙述。
而来到叙述与主题的结合,作者似乎有意把呼啸山庄的人设置成更健全的人:他们或许极端,但行为果敢;或许丑恶,但个性鲜明;或许孤僻,但力量非凡。比如,“希克厉”的原着英文为“Heathcliff”,也有译本译为希斯克利夫或希刺克利夫。“heath”是“荒原”,象征着遍布石楠丛的野外;而“cliff”是“悬崖”,意为呼啸山庄那陡峭的地势。从这个主人公的名字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名深居家中的女子希望寄托的非凡的本源的精神力量。而呼啸山庄之外的人,少了那幺一点灵性,总让人感觉到一种钝性。看似是“老好人”,最后却一败涂地,酿成悲剧。
因此,耐莉和约瑟夫便是两个很好的例证:一个来回辗转于二者之间,既具备呼啸山庄那种独当一面的强势,又沾染上了画眉田庄那种优柔寡断,从而踯躅郁郁,自诩高明;一个对任何冲突都视若惘然,高高挂起,只在乎自己心中的“上帝”。虽然约瑟夫只能够证明在呼啸山庄发生过的历史的原貌,但是也刚好制约了耐莉的叙述;而耐莉对约瑟夫的直接评价,又更加凸显了呼啸山庄人与人之间的冷酷漠然。
“耐莉并不像大家所说的那样忠实可靠,她的叙述和她在两个家庭中的地位同样让人怀疑。”约瑟夫也是如此,除却主题隐喻层面的意义,他更像是用无声的叙述告知读者,那些爱啊、恨啊、复仇啊,在他的眼里,都无非是上帝的安排。虽然这是伪教徒的自私自利的上帝,但是反过来又呼应了结尾的叙述:即通过小卡瑟琳和小欧肖的结合,象征着一切又回到了原点。此时,约瑟夫还是那个约瑟夫,呼啸山庄一切的恶与善的故事于他而言与其说是记忆,更像过眼云烟。可耐莉不同了,她亲历的事情全部变成了回忆,即使因着洛克乌先生的要求而不会尽数烂在肚子里,可“灯下黑”情状总归让结尾的她不再是开头的她。正如三大家族回归原点后,卡瑟琳不再是卡瑟琳,欧肖不再是欧肖了。
可是,多一个管家,再多一个仆从,是故事现实需要还是作者叙述需要,我们无从得知。可也许,恰到好处地把耐莉的叙述视野限制在了约瑟夫的上帝中,真真切切地呈现了一部结构出奇的名作。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8级汉语言文学(师范)本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