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立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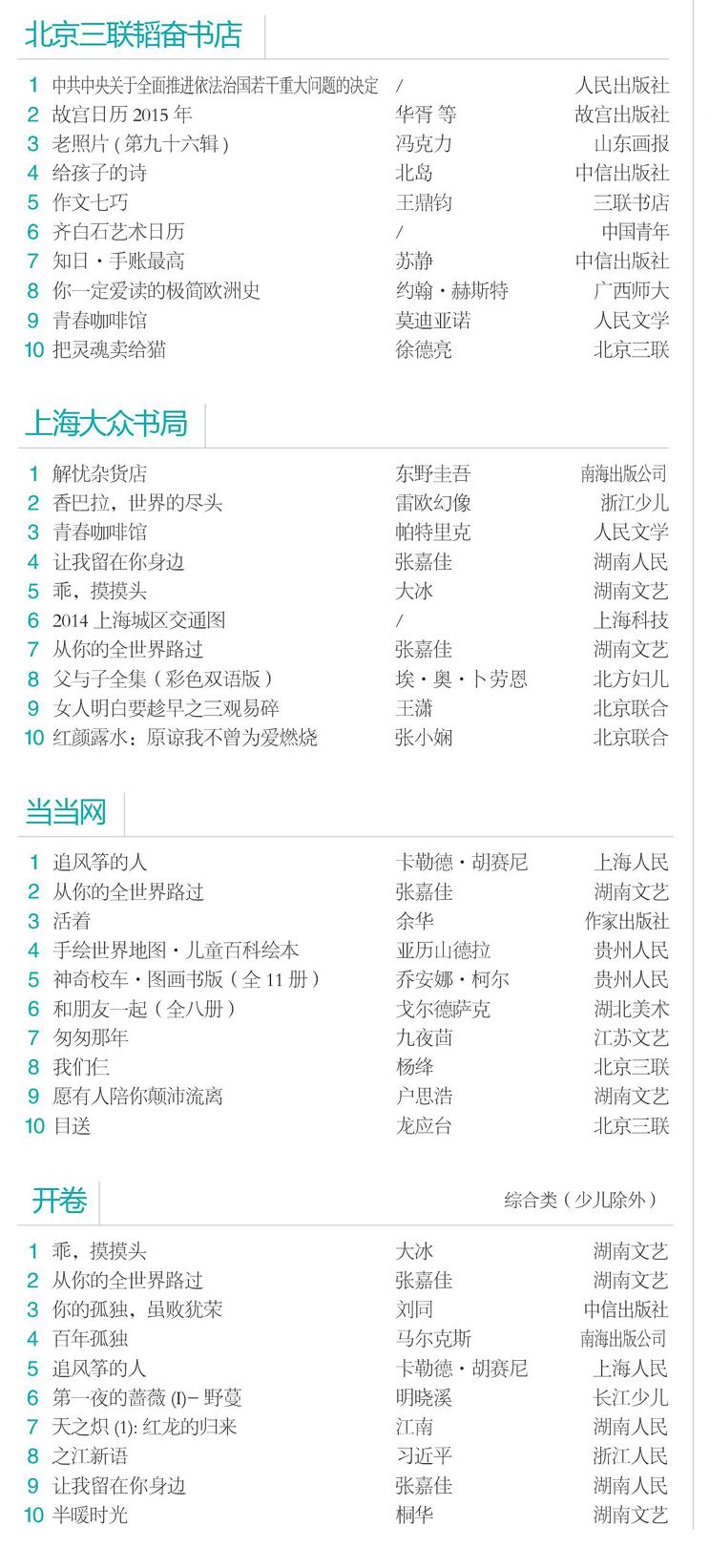



在《爱丽丝奇境历险记》(以下简称《爱丽丝》)的开头,小姑娘爱丽丝说,“如果一本书里没有插图和对话,那它有什幺用呢?”这句话似乎另有所指。我们完全可以把它视为作者刘易斯·卡罗尔的暗示。他的话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没有插画的仙境如何能被称为“仙境”?那样的世界又该是多幺无趣、多幺乏善可陈。诞生于1865年的《爱丽丝》写了一个小姑娘的奇遇,如何在梦中误入兔子洞,又如何引出一连串奇事。大概没有多少人能无视它的魅力,尤其是以想象为第一要义的艺术家。从《爱丽丝》诞生之初,就吸引了各路画家为其作画,其中甚至包括以怪诞、狂野画风闻名于世的后现代主义绘画大师萨尔瓦多·达利和日本的“波点女王”草间弥生。
我们知道,每一位成名艺术家的心里都住着一个天真的孩子,草间弥生也不例外。十来岁的年纪,正是每一个孩子(包括爱丽丝)在自我的仙境里无忧无虑、大冒其险的时段,草间弥生也是如此。只不过比之常人,她的经历更加匪夷所思。10岁时一场意外的疾病带给她永久性的视觉缺损,她的眼前仿佛感染了阿米巴变形虫一样魔幻。不管是美丽的街景,还是漂亮的女孩,在她看来,都只是一些大大小小、颜色奇异的单一圆点的叠加。她的人生也因此被定格在这一瞬间。其后,生理年龄仍在持续增加,心理年龄却从未长大过;身体、外貌日渐衰老,可内心依然天真如一。从此,草间弥生以波点描述世界,也以波点记录故事,于是就有了今天我们熟知的“波点女王”。
其实,草间弥生与爱丽丝的结合并非偶然。一直以来,她就以“漫游奇境的现代爱丽丝”自居。1968年,她更以此为题创作出一系列惊世骇俗的画作。这就可以解释为何曾经让众多密集恐惧症患者备受折磨、大感头痛的草间弥生一旦进入兔子洞里就变得如此熨帖。因为她的波点与爱丽丝的南柯一梦一样具有相同的超现实气质。况且,在草间弥生的构思里,于百无聊赖之际掉入兔子洞从而见证了种种神奇的早已不是卡罗尔挖空心思要讨好的小姑娘爱丽丝,而是画家本人。于是,我们看到这个恢复了少女之身的前卫怪婆婆在波点和幻想的空间里东游西荡。她和故事里的爱丽丝合为一体,时而变大,时而缩小;时而狂喜,时而忧伤;她与微笑的柴郡猫一起攀谈,和半疯半癫的三月野兔共品下午茶,更与动辄取人性命的红桃王后斗智斗勇;最后恍恍惚惚一觉醒来,留下满纸超现实主义的南瓜、张牙舞爪的花朵,和一场美好得一塌糊涂的幻梦。
蔡康永在题为《自愿住进精神疗养院的艺术家草间弥生》的文章中这样写道,“草间弥生不知是在哪面墙上钻了一个洞,窥知了造物者的某个手势或背影,她从此寄居在这面墙上,在两个世界间来回顾盼。”在草间弥生身上,集合了太多奇思妙想。其实,她的创作并不玄妙。一言以蔽之,就是用童话一样夸张的色彩和极富隐喻意味的圆点解构世界,将现实生活里种种司空见惯的事物(比如《老生》
贾平凹的这本新书以一位几近永生不死的唱丧歌的唱师为主线人物,从他的回忆来观看中国百年的朝代变迁与人事变革。本书不仅仅是在讲抗战的英雄故事,而且还在书中浑然一体地交织穿插着古典文化的回响,《山海经》对于中国以千年为纪的山海史怪风物的描写,与《老生》百年历史中四个故事的跌宕起伏相配合,不但烘云托月相映生辉,更有在时过境迁后参透人世的坦然。
南瓜、蘑菇)高度提纯,然后不断地扭曲、重复,再扭曲、再重复。这就像是魔咒,丰富了言语之外的留白与所有想象的空间。爱丽丝亲身经历过的与她从未经历过的冒险,都被这些个浓艳得几乎要从纸上跳出来的圆点塞了个满满当当。
以现代眼光看来,出版于1865年的《爱丽丝》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与卡罗尔的大胆创新不无关联:在19世纪中叶死气沉沉的社会环境里,他敢于打破僵局,以爱丽丝系列首开奇幻先河。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可以在后世诸多作品(比如《绿野仙踪》)里轻易地找到爱丽丝的影子。从这种意义上说,1865年的卡罗尔与今天的草间弥生确实有高度契合之处。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这是叶永烈继《邓小平改变中国》和《毛泽东与蒋介石》之后又一部纪实力作,这是一部党史,也是一部革命史,一部精神奋斗史。为写这本书,叶永烈奔赴井冈山、瑞金、遵义等地,访问了众多历史见证人、知情人和中共党史专家,查阅了大量有关的历史文献、档案,以翔实、流畅的笔调,从领袖史的特殊视角解读毛泽东的传记经典揭开重重迷雾,披露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沉浮命运。
《波西米亚玫瑰的灰烬:萧红传》
萧红仿佛一个中国的波西米亚人,终其一生都在为了自由而流浪。除了童年,她不曾有过世俗意义上的幸福。从哈尔滨、北京,到上海、武汉,再到重庆、香港,从异乡到异乡,从一个男人到另一个男人。每一次抉择,她的人生都有了新的局面和境遇,却终究是痛苦比欢乐多。邹经这部《萧红传》,对传主灵魂的高度深具同情的理解,将萧红一生的苦难娓娓道来,让我们重新发现“另一个萧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