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茹花 张宝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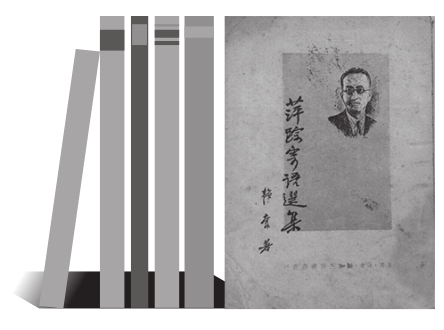
随着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爆发,曾经备受追捧的资本主义制度设计大幅失去了吸引力。与此同时,经过十月革命洗礼的苏联,在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政治成就,从世界各国中脱颖而出。当时的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夹缝之中,民族的前途和出路问题成了中国知识界的关注焦点。邹韬奋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中踏上了赴外之旅。他因公开批判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而被列入逮捕名单,便于1933年7月前往欧洲。以新闻记者的身份走访英、法、德等国之后,他于1934年11月到达苏联,而后于1935年5月再到美国,8月离开美国回到中国。这期间,他将自己在欧洲和苏联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皆以新闻报道的方式记录下来,后经整理编成了《萍踪寄语》,又于1937年凭借记忆完成了《萍踪忆语》,记录了他在美国的经历和感受。邹韬奋尽管在美国只逗留三个月,在苏联仅住了两个月,但他凭着新闻记者的敏锐眼光,准确把握住了两个国家的发展态势。对比阅读集中书写苏联的《萍踪寄语(三集)》和集中书写美国的《萍踪忆语》,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邹韬奋对美苏两个大国及其不同社会制度的态度,而且可以明了他作为先进知识分子表达中国现实关怀意识的曲折路径。
邹韬奋视察美国期间,见识了世界上最富有的都市——纽约,查访了统治全美经济生活的金融大本营——华尔街,体验了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也了解了貌似民主和平等的社会制度。但是,他深入探寻之后发现,这个看似光鲜亮丽的“金圆帝国”只是虚有其表而已。它标榜民主和平等,但种族歧视盛行。除了种族压迫,阶级剥削也愈演愈烈。美国的阶级分化,正如邹韬奋所描述的那般窘迫:
所可比较的是这些阔人家的享用和在贫民窟所瞥见的凄苦状况,一是天堂,一是地狱。这两方面的人,一方面是靠着剥削他人血汗所获得的利润;一方面是靠着出卖劳力来勉强过活。
邹韬奋笔下的美国社会,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少数富人的天堂和多数穷人的地狱”。繁荣是那些中饱私囊的资产阶级眼中的繁荣,而要了解真实的美国,却得深入社会最底层,了解底层人民的生活状态。我们阅读邹韬奋的文字,可以充分感受到最底层人民受尽剥削和压榨之后的穷苦和悲惨,了解这个“金圆帝国”繁华背后的狼狈和落魄。用杜甫的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来概括美国的社会惨状,恐怕最为合适不过。邹韬奋在《萍踪寄语(三集)》的“弁言”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已经陷入了“生产力的进步和生产工具私有的社会制度不相容”的尴尬境地。
苏联之行却带给邹韬奋另一番体会。他初登“西比尔”号前往列宁格勒,发现船上虽有等级舱之分,但不限制各等级舱之间的来往,船上设备人人皆可利用,环境相对宽松许多。到苏联之后,他参观了设备齐全的中央文化休养公园,为完善医疗设备而专设的夜间疗养院,为解放家庭对妇女的束缚而设的托儿所和幼稚园,为工人及平民提供休闲娱乐的休养胜地克里米亚……作者所到之处,均可见证苏联渐趋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除了社会福利,苏联的工会制度、农业生产、教育状况等也让邹韬奋颇为心仪。他注意到,工人拥有自己的工会,生产资料属于全体工人所有,工作时间合理;集体农场非常普遍,无论是贫民还是富农,都需参加集体生产;苏联重视培养青年一代,不仅因材施教,开发学生全面发展的潜能,而且着力实现教育大众化和公平化。
在邹韬奋看来,苏联尽管依然无法彻底根除沙俄时代滋生的社会弊端,但整个国家发展势头强劲,日新月异,处处充满了生机勃勃的景象。勤劳的工人和农民,活泼积极的青少年,蒸蒸日上的工农业,处处洋溢自由和平等的气息。这是一个人人平等、人人共享的国家,是一个正在积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是一个前途光明、呈现欣欣向荣景象的国家,是真正将民主、平等、自由等理念有效付诸行动的国家。
邹韬奋笔下的美国,空有繁华的外表,虽为“金圆帝国”,但资产阶级依旧极力剥削贫苦工人和农民,社会贫富差距巨大,社会矛盾尖锐;而苏联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建设进展迅速,一改往日封建落后的面貌,正在成为世界上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美国都是当时在世界上拥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大国,但是为何作者看待两者的态度如此迥然不同,进而构建出近乎对立的异国形象呢?
九一八事变后,在严酷的阶级斗争和中国革命实践的教育下,邹韬奋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觉悟迅速提高,开始从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转变。他游历欧洲期间,实地考察了一些渐趋没落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带着对资本主义的这种消极心态,他来到了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苏联之行给作者留下了一段还算不错的旅途记忆。抱着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作者又来到了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阐释学中有一术语,叫“前理解”。也就是说,由于受到某些主观或者客观因素的影响,人们在真正接触到一些事物之前,就已经对其形成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邹韬奋未到达美国之前,就已经见证了老牌资本主义的没落和新兴社会主义国家的崛起,所以,在他的印象中,美国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同样难以避免衰落的命运,而社会主义的崛起已然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
20世纪20年代末爆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给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以沉重的打击,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对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开始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经济因为受到大萧条的牵连而日渐凋敝,再加上外有异族入侵,内乱不断,人民的生活水深火热,中华民族危在旦夕。像邹韬奋这样的先进知识分子不仅对国民政府感到失望,而且为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感到深深担忧。他真切希望可以寻找到一条救国救民、富国强兵的道路,让整个中华民族从压迫和剥削中解放出来。苏联成功的革命实践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犹如一盏黑暗中的明灯,重新点亮了他心中的希望。
邹韬奋的文字浮面所写的是他在美苏的见闻,但是细读文本我们可以发现,他在叙写这两个客体的同时,常常联想国内诸事,并分别做一番饶有趣味的评说。比如,他在述及观看《列宁的三歌》的感受时说,列宁的后继者们“努力使社会主义一日千里,不负列宁的付托……我同时不禁联想到有的国家里在革命领袖死后,便无恶不作,弄得丧权辱国、民不聊生,老实跑到反革命的路上去,却腼然不以为耻的后继者们”。诸如此类的议论,无不表明他作为先进知识分子的深切现实关怀意识。
在《萍踪寄语》初集的“弁言”里,邹韬奋曾提出过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世界的大势怎样?第二个是中华民族的出路怎样?”美国和苏联就像两面相对而立的镜子,邹韬奋立于两者中间,分别通过两面镜子打量着,思忖着,抉择着。可以说,看似是流亡欧美和苏联的旅行,其实于他而言,是一场身负严肃使命的解惑之旅。邹韬奋在《忆语》的“弁言”里写道:
世界上有三个泱泱大国:一个是美国,一个是苏联,一个是中国。……它们对现在和将来的世界大势,都有着左右的力量!
也就是说,“世界大势”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出路”的选择,而“中华民族的出路”则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着“世界的大势”。归根结底,“中华民族的出路”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如果说在《萍踪寄语(三集)》中,邹韬奋亲身感受了政权独立、人民幸福的苏联后由人及己,时时感慨国内的悲惨现实,那在《萍踪忆语》一书中,他已不再停留在思想批判的层面,而是流露出了更加明朗的态度。在从伦敦开往纽约的轮船上,邹韬奋同一位“老印度”交谈后发表感慨道:
我们看到欧美各国的一般人的生活,拿回来和中国人的生活比较比较,没有不感觉到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简直不是人的生活。……我们要铲除剥削多数人而造成少数人享用的不平等制度,树立功劳共享的平等制度。
在写到美国青年时,作者更是集中表达了改变中国现实的迫切愿望:“这一群孩子们……对于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都有深切的兴趣和恳挚的同情”,他们觉得中国“一旦翻过身来,给世界的前进动力,不知道要伟大到什么地步!”这种热望让他感觉既兴奋又惭愧。兴奋的是在这样一个遍布剥削、压迫和歧视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有一群进步青年和他一样关注着中国的前途。然而,中国当局者却软弱无能,任祖国的国土被异族蹂躏践踏。这让他感到万般惭愧,进一步坚定了他积极参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决心。
邹韬奋认为,“法西斯的风行和备战的狂热”尽管是“欧洲最近的实际情势”,但这只是日暮穷途的资本主义最后的挣扎。明确了“世界的大势”,紧接着就是考虑“中华民族的出路”。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的民族,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开展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而要开展斗争,就必须考虑中心力量和斗争策略这两个问题。对此,邹韬奋也给出了自己的见解。依他看来,中国决不能依附于帝国主义,依靠他们的代理人和寄生虫,而是要靠中国自己的勤劳大众,因为只有“这样的中心力量才有努力争斗的决心和勇气”。解决了中心力量的问题,接下来就是斗争方略的问题了。他认为,民众团结一心,奋起反抗,才是正途。这样做,中国不仅能获得自身民族的解放,还能造福于其他民族,就像苏联的革命实践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国指出了一条充满希望的道路一样。
《萍踪寄语(三集)》和《萍踪忆语》虽属报告文学,理应有很强的客观性,但是,再强的客观叙述也免不了掺杂作者的主观情感。何况,邹韬奋生活在动乱的20世纪30年代,不是一名普通的新闻记者,而是背负着特殊的时代使命。他业已形成的价值取向,自然而然会导致他对新闻材料做进一步的筛选和编辑。就此而言,两部作品构建出的对比鲜明的美苏形象,就成了邹韬奋客观叙述和主观情感合力的产物。他写作的用意非常明显,只有弄清当时世界的大势,才能思考中国在世界如何自处的问题。因此,观察异国、书写异国,也成了邹韬奋思考中国问题、表达现实关切的重要策略。正是通过这样的策略性书写,他彰显了作为现代进步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作者简介:王茹花,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张宝林,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