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汉秋
在文化的三个层面中,吴敬梓的杰作《儒林外史》不经意于物态文化层,不停留于制度文化层,而是着意于精神文化层,这就深入人心人性的深层,从而超越时空给人良多启迪。境界就是一种精神状态,《儒林外史》着重展现了三种人生境界:功利境界、天怀境界、觉醒境界。
一、功利境界
《儒林外史》涉及的社会层面虽然很广,但正如鲁迅所说:“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吴敬梓根据自己长期的体察和分析,描绘了一轴色彩斑斓的士林人物长卷。功利,在士林就是功名富贵。“功名”的概念在明清科举时代常用以指科第及由科第取得官职。
中国的传统统治者积累了运用利益驱动机制的经验,特别注意把读书与功名富贵联结在一起,通过科举制度使读书人“入我彀中”。“学而优则仕”成为封建时代读书人的群体价值取向,马二先生就是这个模子里倒出来的“正宗产品”。他说,就是(孔)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否则)哪个给你官做?他以拙朴的本性毫无讳饰地讲出老实话:念文章、做举业,就是为了做官。只要能做官,朝廷叫做什幺举业,就做什幺举业。至于这种举业是否合理,那他根本不去想,能做官就合理!封建统治者正是充分发挥权力的魔法,使读书人乖乖地做自己的顺民。《儒林外史》没有停留在科举制度这个层面,而是继续深入下去,写到读书人的精神层面:思想如何被戕害,智能如何被斫伤,人格如何被奴化,结果形成了依附性和奴性,把读书和做学问限制在为官方的制度、政策、功令进行诠释、宣传和鼓吹的范围之内,失去了“士”作为人类理性和“社会良知”之代表的独立思考能力。周进、范进就是明显的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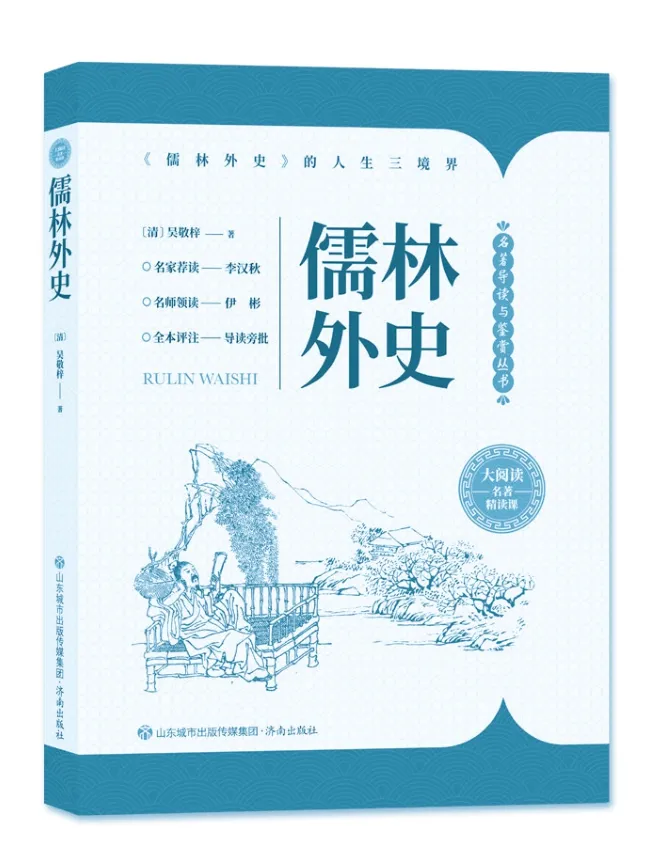
沿着马二先生所鼓吹的科举正路——秀才、举人、进士,做官——一头钻进去走到极端,思想发生偏执,就会产生周进、范进。周进考到六十几岁连秀才都没进,还是个童生,所以没资格进贡院考举人,他有一回到南京贡院,看到号板就撞号板痛哭。范进考到五十几岁,突然中举了,高兴得发了疯。这都是由热衷发展到偏执。还有一些更糟糕的人,可以叫作“陷溺者”,他们人格扭曲、分裂、堕落,被异化成“非人”。沉迷者和陷溺者造成的世风是什幺样的呢?吴敬梓对“势利”和“伪妄”特别敏感、痛恨,因此揭露讽刺得特别尖锐、深刻。
鲁迅塑造的阿Q是“精神胜利法”的精神现象典型,吴敬梓塑造的胡屠户则是势利精神现象的典型。范进是他女婿,中举前是范进,中举后还是范进,但因“势”和“利”大变,胡屠户的态度也就大变。中举前他骂范进说:“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举凡轻蔑人时,一般说“你该拿镜子照照”,而胡屠户却说“你该撒泡尿照照”,轻蔑至极,刻薄至极!奚落人时一般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而胡屠户说“想天鹅屁吃”,这又是极尽鄙薄挖苦之能事,癞蛤蟆还能想吃天鹅肉,而范进只能想吃天鹅屁,连癞蛤蟆的资格都没有,胡屠户根本就不把范进当作人。范进中举后他却说:“我每常说,我的这个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里那张府、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中举前他对范进动不动“一口啐在脸上,骂了一个狗血喷头”;中举后“现世宝穷鬼”一下子变成“贤婿老爷”。“贤婿”是老丈人称女婿,“老爷”是奴才对主子的称呼,把这两样称呼不伦不类地加在一起,本身就极不和谐,把胡屠户的奴性、势利讽刺得体无完肤。
还有一些品性恶劣的官僚乡绅,打着儒家纲常伦理、仁义道德的旗号,却弃道而嗜势、忘义而贪利。五河县的方乡绅、彭乡绅、唐二棒椎、唐三痰之辈,像蛆虫一样张皇,“礼义廉耻,一总都灭绝了”!把这号人的恶德恶行表现得最充分的是严贡生。他运用乡绅的势力、讼棍的狡诈、无赖的手段,一门心思作恶,每个毛孔都渗出罪恶的毒汁。他们是儒林中最腐朽的一部分,吴敬梓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满怀憎恶地向他们喷射严冷辛辣的讽刺烈焰。(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