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柳林
尤金·奥尼尔(1888—1953)是美国戏剧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作家,他领导的小剧场运动和严肃戏剧创作为世界剧坛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毕生刻苦创作了二十一部独幕剧和三十部多幕剧,凭借着被誉为“标准的现代悲剧”——《天边外》首次问鼎普利策奖,随后又凭借《安娜·克里斯蒂》《奇异的插曲》《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又三次获得普利策奖,并把美国的戏剧提升到文学的品格。他的剧本不仅在本土剧场上演,而且很快地传遍了全球的角落,成为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位美国剧作家。
《诗人的气质》和《更庄严的大厦》是奥尼尔创作的连台历史剧《一个占有者自我剥夺的故事》中硕果仅存的两部剧作,也是作家从创作中期向晚期的转型之作。它延续作家寻找归属的主题,进一步探索净化灵魂之道。19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物质欲望膨胀、拜金主义思想膨胀的历程,表现为昔日的精神家园日渐失落,人的灵魂无所归依。正如布伦达·墨菲在其收录于《剑桥美国戏剧史》中的一篇文章所指出,当尼采宣告“上帝死了”,西方传统基督教信仰的瓦解带来了社会秩序的紊乱。在20世纪20年代,奥尼尔也在追寻他所谓的“神的替代品”,作家用戏剧的形式书写被金钱和欲望腐蚀灵魂的人物形象,透过人物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交易与抗争,揭示精神危机笼罩下,个体寻找自己在社会中适当位置的艰难历程。
移民文化下的身份定位
尤金·奥尼尔出生于纽约百老汇的一家旅店,其父母是笃信天主教的爱尔兰移民,因此爱尔兰移民的身份贯穿于作家一生的戏剧创作。在《诗人的气质》和《更庄严的大厦》中,奥尼尔鲜活地刻画了以科尼利厄斯·梅洛迪为代表的爱尔兰移民为捍卫爱尔兰文化而不断奋斗的过程,同时赤裸裸地展现了以梅洛迪为代表的传统欧洲贵族与以哈佛德为代表的美国新兴资产阶级所产生的激烈冲突。作家赋予梅洛迪身上失去归属感的影子,正如梅洛迪回顾过去孤独的悲惨生活时所说:“基督作证,这位少校要不是天下的大笑柄才怪呢。愿上帝让他那在烈火中受煎熬的灵魂安息吧!”作家面对个人与社会无法协调的困境,展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解决之道。
主人公科尼利厄斯·梅洛迪祖籍爱尔兰,因致一位农村未婚少女怀孕,移居美国。来到美国后,他依然沉浸在往昔的“荣誉”中无法自拔,经常吟诵着拜伦的经典诗句,并且竭力要求女儿改掉爱尔兰口音。梅洛迪又想亲近本民族同胞,为爱尔兰乡邻提供免费的酒,却禁止他们直接通过大门进入客厅来保持尊严,来彰显绅士身份的尊贵。
梅洛迪与哈福德的决斗使他开始清醒意识到“梦破灭了,诗人被毁掉了,剩下的只是一个爱尔兰农民”,灵魂失去了寄托。爱尔兰农民的身份所带来的困境让他从根本上丧失了话语权,无法与向往的上流社会建立平等沟通的交流。他不惜用手枪打死了象征虚荣心的骏马,埋葬掉战功卓着的光荣,被迫甘心做一个邋遢的小店主。

女主人公萨拉则在文化的冲突中,突破传统爱尔兰价值观的束缚,主动迎合美国主流文化。她不仅毁掉父亲梅洛迪身上的诗人气质,而且摧毁丈夫西蒙的诗人理想,将他改造成一个商人。在《更庄严的大厦》中,她一跃成为家庭的主宰,腐蚀西蒙的理想,用物质上的成就肯定自己,完成价值观的转化,反映了移民的本民族文化在美国现代物质文化冲击下的不断溃败之路。
连台剧虽然主要写的是一个美国家庭的故事,也是美国历史的反映。移民既与本民族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又在社会交往中,同其他民族建立起新的联系。梅洛迪处处表现“优越”的一面,其隐藏在面具下的实则是身份失落带来的自卑,只能用幻想与酒精麻痹自己。剧本末尾,梅洛迪幻想破灭了,认清自己所面对的现实,实现了从诗人到酒店主的转变,但不久便因郁郁寡欢而死。从更深层次来说,《诗人的气质》的结局是理想与残酷现实的妥协,是透过梅洛迪装腔作势的痛感传递出来的。萨拉的成功则反映出两种不同价值观碰撞中,移民的传统价值观被美国现代物质主义价值观同化,金钱逐渐成为灵魂的主导者,指导人物的行为。在《更庄严的大厦》中,萨拉意识到美国梦不过是物质的成功梦,也将在物质主义的侵蚀下彻底崩溃,明白了幸福才是生活的真谛。
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对峙
西蒙在萨拉的诱惑和外在压力的共同作用下,理想主义很快被拜金主义俘获,家庭关系被冷酷无情的金钱交易取代,凸显出人性的贪婪。他在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对峙中,以交换价值作为衡量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唯一尺度。
西蒙是哈佛大学毕业的富家子弟,不顾家人的反对,自我放逐到湖边的小木屋中思考问题和写书。为了保障灵魂的自由,他竭尽全力地远离现实生活的喧嚣,使想象的世界成为灵魂的寓所。为了寻求社会的认可,他从鄙视金钱、物质的身份转化为不择手段夺取利益的商人和赌徒,沦为权力和财富的奴隶。这一转变虽然会受到心中的幻想的召唤,但还是冲破人的自觉意志和理性的束缚,使欲望在外在世界和内在心灵的较量中取得胜利。
奥尼尔不表现人与上帝的冲突,而是通过西蒙前后生活对比呈现痛苦的精神状态,着重描写现实的“我”与过去的“我”的冲突,揭示隐藏在生活背后“不可思议的驱使力量”。在作者眼中,人们信仰超自然神或上帝,认为人的命运无法摆脱其控制,但随着生产力的迅猛发展,金钱和物质渐渐占据信仰的位置,却又无法真正取代信仰,从而导致精神遭受巨大的幻灭。

西蒙的灵魂觉醒受到母亲黛博拉和妻子萨拉两股不同力量的拉扯。一方面,天生梦想家的黛博拉过着远离世俗的生活,督促儿子从烦闷中逃遁到书本的世界,为西蒙营造了诗意的生活空间;另一方面,萨拉由于出身卑微和父亲“贵族梦”的影响,充满对权势和荣誉的渴望,引导改变西蒙的生存取向。欲望所产生的神秘力量支配着西蒙的命运,他所追求的诗人梦在外部环境挤压下变形,真实的人性被真实的现实异化。为了满足萨拉对物质的占有欲和虚荣心,西蒙抛弃梦想,抛弃人性的善良,变得冷酷和狡诈,贪婪地占有金钱和土地。戏剧家奥尼尔深入生活,让有血有肉的人物与社会问题尖锐碰撞,不仅表现人的灵魂在现实与幻想之间的领域中失落之后所遭遇的一切,记录金钱、欲望对个体的人造成的心灵创痛以及被抛离的孤独感,而且善于捕捉人物的心态。西蒙随着灵魂的错位身体也愈加虚弱,情绪变得惊慌失措。在剧本的尾声,萨拉带着西蒙到农场回归简朴的生活,摆脱贪婪,重获自由,体悟到相亲相爱才是人间最大的财富,完成了灵魂的觉醒。
事实上,人在物质至上的社会失去与自然、精神的和谐,人性的高尚粉碎之后,“失去自我”是必然结果。因此,奥尼尔说:“杨克(《毛猿》的主人公)实际上是你自己,也是我自己。他是每一个人。”人类只有通过不断的灵魂拷问才能确立现代个体独立自由的自我意识。
灵魂的救赎
奥尼尔早年放弃了对宗教的信仰,长期通过一系列作品坚持寻觅“新的上帝”,对人生的奥秘进行新的探索。他认为今天的剧作家必须挖掘出自己感受到的当代病根——老的上帝已经死去,科学和物质主义也已经失败,它们不能为残存的原始宗教“本能”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新上帝,以找到生活的意义,安抚对死亡的恐惧。这表明,奥尼尔正为处于信仰危机和拜金主义盛行的美国社会积极寻找新的精神支柱,不断向自然时空开拓,向原始信仰回归。
尤金·奥尼尔善用细腻的笔触描画时代的不幸与危机,在《诗人的气质》和《更庄严的大厦》中,展现人类为了追求物质享受而使灵魂处在一种焦虑和无所依傍的状态,逐渐走向绝望的深渊。尽管如此,作者对灵魂完成救赎和人性的回归仍然寄托希望。在剧本第四章第一场中,西蒙凝视着萨拉设计的新府邸的图纸,脱口朗诵了美国浪漫主义诗人奥利弗·霍姆斯的诗句:“给自己建造一所更庄严的府邸吧,我的灵魂,既然时光飞逝不停!”
奥尼尔笔下的人物渴望在自然的怀抱中找到归宿,花园中的凉亭是黛博拉自我救赎的地方。“小木屋”是西蒙在经历商场的扩张失败后极力找寻自我和谐的疗伤之地,重温了自然的魅力和自由,从而找到了心灵的安宁。真正的大自然情境能让人与自然进行心灵的对话,纯洁、和谐的世外桃源可以使人超越所有的欲望,安抚躁动的灵魂,生命亦可通过自身的修行和修炼,返复到始初的状态。“回归”到原始生存状态,可以看出作者将东方道家思想作为一种拯救的尝试。道家思想强调清静无为,不执着于世俗的行为,不希冀虚幻的事物。这与萨拉对孩子们的期望“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干吧”不谋而合。因此,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也是内心的折射,自然象征人类最终的依托和精神家园,体现了奥尼尔强调人类融入自然的生态伦理意识,在自然中重新找到自我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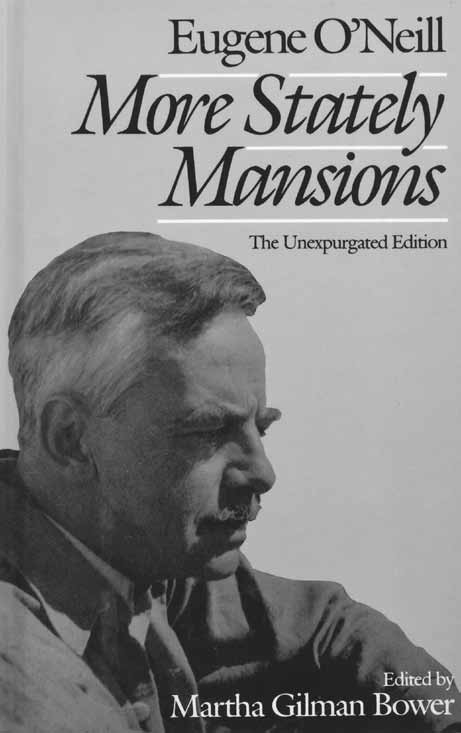
奥尼尔曾经说过:“在我的全部剧作中,罪孽必受惩罚,并得到救赎。”他不是站在上帝的高处去审判灵魂,而是让人物在自我探索中寻找人性和良知。《毛猿》的主人公杨克直到死于猩猩之手才找到自己的价值,看似悲剧,实则作者用决绝的方式表现出人类生命强大的内在动力和对生存困境的抗争,迸发出震撼人心的审美力量。而在《诗人的气质》和《更庄严的大厦》中,西蒙和黛博拉在回归现实社会的过程中都经历了象征性的死亡。西蒙经历失忆过程重生,黛博拉精神失常而离世,两者的根本原因都是理想和现实抗争的失败。西蒙在一次次的痛苦较量中,选择回到最初的小木屋赎罪,表现了主人公在困境中寻找现实出路时内在灵魂的渴望,努力从悲剧宿命中寻找对抗命运的力量。这说明,奥尼尔认为人的生存需要幻想,失去幻想,也就失去了生活。乌托邦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寄托,也是人在物质追求以外必须持有的精神追求。乌托邦是对至善价值的追求,对不满现实的反叛、逃避,尚不能足够解决现代人心灵匮乏的问题,但也为建设精神世界发挥重要作用。
“我们想方设法占有灵魂以外的东西,虚掷了灵魂”,这与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形象的意义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只有呼喊信仰的树立,叩问人性本原,摆脱贪婪对自身生存的桎梏,让诗意和热情展示出救赎灵魂的力量,才能让灵魂有所栖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