桫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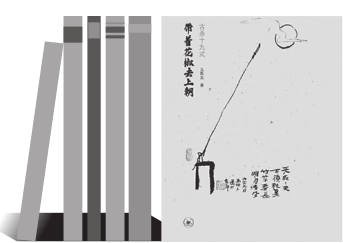
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吗?略略一说这好像不是问题,细究起来却是个大问题。何兆武先生就此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历史学是科学吗?》。文中说,历史具有两重性,一重是它的自然性,这是科学的一面;另一重则是它有着非科学的、人的主观意志成分。既然历史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那么问题就来了:我们对历史的表达究竟是一种科学表达还是美学表达?我们知道,对科学规律的表述不能有任何主观的成分,历史叙事显然不符合这个条件,因此它只能是一种美学叙事,是人类将历史当作审视对象的审美表达。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叙事就有着文学叙事的特征。尤其是在微观史学或对历史片段进行细部呈现时,这个特征更明显。继《提头来见:中国首级文化史》之后,最近马陈兵出版了第二部与这一主题相关的著作《带着花椒去上朝:古杀十九式》(三联书店2020年6月版,下简称《古杀》),从对中国古史图籍中与杀戮有关的浩繁资料极为专业辛苦的爬梳入手,以“杀”——摧毁生命这一崭新视角,借由生杀之机,展开对中国历史文化上一处处“杀风景”的“科学”描述与呈现,深层传递的则是对历史独特的审美体验。
“文史一家”是中国史学的传统。自《春秋》《史记》等正史以降,包括形形式式的野史志怪,都或多或少体现着这个特点。刘知己“文之与史较然异辙”立议,绝难匹敌“良史莫不工文”的深远影响。过去的观点认为,文学在历史书写中起到的作用,是使记述和描绘充满美感,即所谓“史之赖于文也,犹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例如评价《史记》时说:“从文学的角度讲,它第一次运用丰富多彩的艺术手法,给人们展现了一道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廊”(中华书局“中华经典藏书”《史记》前言,韩兆琦译注),而在新的史学观念中,对历史规律性结论的论证和建构过程及其方法也应用着文学的技法。在史料充分翔实、论证严密准确的前提下,将“文史一家”的人文传统或曰表达范式,落实到历史的个案研究与微观叙述上,建构出“文史合一”的史学新文本,置凉冷之逝波于滂湃激越的审美聚光灯下,借此强烈传递人文关怀与学术抱负,更为有效凸显历史与现实生活与现代社会的深层勾连,是《提头来见》与《古杀》二书的一家面目和重要特色。在书中,马陈兵既以一位历史学家的专业操守尊重史料的严肃性和辨析的严密性,又不吝于以一位文学家的活泼和敏感对历史施以温暖的情感关照。首先,在保留必要的学术概念与逻辑构架基础上,他善于发现并巧妙选择审美视角,辅以文学性的语言,形成了别具一格充满诗意的文史话语风格。作者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中国历史上的非正常死亡问题或曰杀人事件、杀人方法,赖以成书的材料充满残忍和血腥,流血飘杵的历史长河遮蔽而亦涌动着亿万个体在王朝权力维系与更迭中卑微的生存与多舛的命运。作者对每一个纳入书中的杀人事件、杀戮类型条分缕析,力图从细节上描摹历史的场景——当然真相已不可还原,作者展示的只是可能性。作者仿佛是一位说书人用讲述性语调微微道来,不仅细述原委,也以自我的立场展开充分而犀利的评判。这其中,不仅对现代人看来诘曲聱牙的文字史料进行了一番当代解读——甚至不惜使用流行的俗语,同时作者毫不遮掩的主体身份和视角亦增加了个人化的情感色彩。这类例子在书中俯拾即是,仅举一例,在“天杀”一节中,后晋太原王刘知远称帝后顺手沿用了“天福”这个早随石敬瑭寿终正寝的年号,作者引用刘皇帝自己的话做了解释之后说:“看看,捡漏儿太快,自己都脸红”,对历史当事人满带着揶揄和讽刺,这种语气就是批判的态度。在这一节中还讲到“太白昼见”这一天文现象在统治者那里造成的影响,作者说:
新朝多事,原太子和老皇帝接连死去,新皇帝刚继位,政权很不稳定,此时“太白昼见”,这信息扩散出去,完全可以理解为上天给后汉这只颠簸渗漏的新船一个必将颠覆的判决,真是往伤口上撒盐,让当权者极为忌怕,难怪当天就有人因为抬头多看了几眼天,被拦腰一劈,横尸街市。
这段话极尽戏谑,在抨击当权者的愚昧和控诉一场荒谬的滥杀中表现出愤懑的情绪。
在对历史的美学表达中,文采只是面子活儿。马陈兵作为历史学家的真功夫,是用审美化的叙事建构历史——并不是说人类所有的叙事都与文学暗通款曲,但历史叙述中的叙事,是“文”的审美表达范畴的扩展,这体现在对历史的意义建构以及在这个意义框架下对历史实践的理解上。该书认真查考了史料上诸种令人丧命的主动或被动的行为、方式,将其归纳为椒杀、毒杀、歌杀、酒杀、笑杀、饿杀等十九种——为每一种方式配上“杀”字,既揭露出统治者对生命的轻蔑和偶发的自然灾难毁灭生命的悲剧,也包括个体的自杀。在对“杀”的方式的提炼上,作者采用了归纳、推理和总结这些科学的方法,但作为建构“杀”的历史的重要法门,其中充斥着的象征、隐喻、引申等修辞手法与科学不沾边儿,纯然是作者的文学之笔。例如在对“井杀”的探讨中,作者在章将读者引向地上的水井:
井其实是除黄河、长江之外中华民族的第三条母亲河,它平时养育亿兆生民,乱世生灵涂炭时,既能为一心赴死者提供解脱法门,亦可藏生天于杀地。
但在讨论秦、魏等六个王朝如何被“杀”于井中时,天上星宿诸井与地上棋布之井、象征之井与真实之井已恍兮惚兮,打叠映射,而这正是观念史衍生、发展的真实路径与题中之义。例如汉代秦之际,《汉书》追述说汉高祖正是从“五星聚于东井”的天象中获得了“受命之符”;而到了曹魏时期,天上的井移到了地上,全国多地报告说龙见于井,尽管曹魏统治者极力把舆情往祥瑞上靠,篡夺之势已成的司马氏集团自可从《汉书》刘向的解释中另得其解,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龙困于井”乃是杀兆。举凡内生于历史叙事的生机杀律,不过延续了历史本身的逻辑:通过修史为统治者“奉天承运”建立合法性,自是封建帝王攫取权力心照不宣的秘法,相应的方法回应响应着帝王贪恋权力的心理欲求,这与文学表达并无二致。而专制权力面前的草芥小民和朝廷重臣,都难免对应到十九道选择题的一个答案中,这才是生命的孱弱与悲哀。
罗新在《历史学家的美德》一文中讲道:
历史是对过去的讲述,无比巨大、混沌一团的过去中被赋予了秩序和意义并且被讲述出来的那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才是我们所说的历史。被讲出来的历史就不再等同于过去;过去的无数方向、无数线索被简化成历史的单一方向和单一线索,过去无可记数的参与者被简化为少数人群及其精英,主人公和中心人物出现了,目的和意义诞生了。
在马陈兵的新书中,大量至今读来仍然令人恐怖不安的“古杀诸式”与案例被聚合在一起,结构叙事的方式是顺着历史中隐伏着的生杀之机来进行的,如作者所言:“家国存亡之外,生杀倚伏之机,也每每成为人物和事件的关捩与看点,贯穿于历史的书写与解读中。”除了学术的稽钩考证,该书深层的旨趣是通过对史书上满纸杀事的追问来凭吊和敬挽生命的尊严,这才是作者更乐意让读者引起共鸣、思考的情怀和追求,亦是以之比附“古诗十九首”的苦心所在。作者在该书后记中坦言,《带着花椒去上朝:古杀十九式》是《提头来见:中国首级文化史》的“副产品”。在上一部书中阐述礼教中国如何借助“首级”这个特殊介质建构“礼兵刑三位一体”统治机制之后,这部书放下了逻辑严密的史学论证,在每一桩杀人案、每一种杀戮方式中体味历史的冷漠或温情,更给人以美学意义上的启迪。作者因此说:
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具体而微的“杀人的动机”往往并不重要,“动人的杀机”——生杀消长的本质关联与内在因果——才天机出透。
既然历史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那么历史前进的方向又在哪里呢?何兆武先生在同一篇文章中说:“历史乃是彻头彻尾的目的论的,历史是被人们有意识地在朝向一个目的而推动的。”我们无法预见未来,左右天机,唯愿每一个善良的生命都得以体面地活在静好现世。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网络文艺委员会委员、河北作协文学院研究员。)



